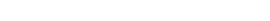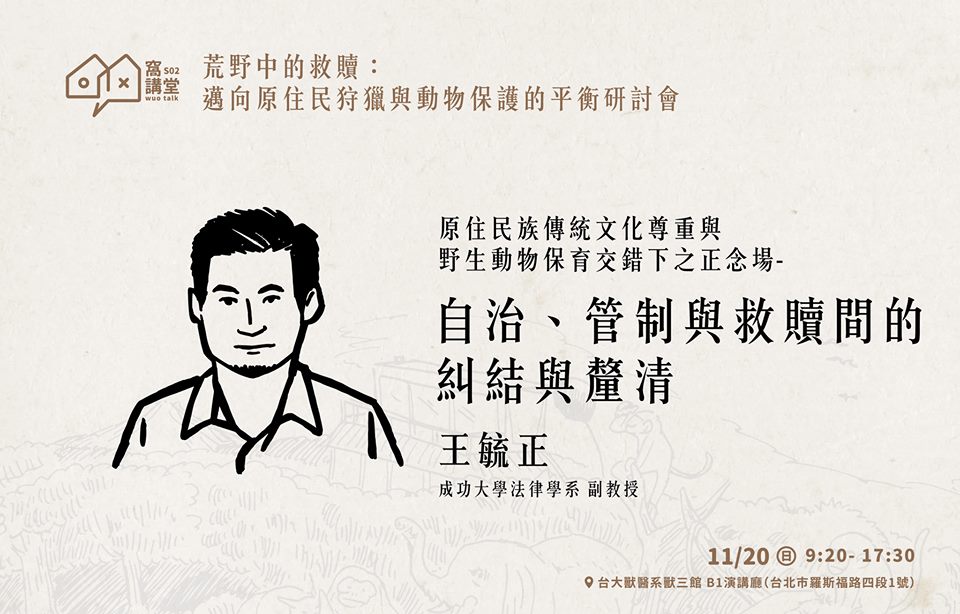【荒野中的救贖08】
講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尊重與野生動物保育交錯下之正念場
─自治、管制與救贖間的糾結與釐清
講師:王毓正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胡慧君整理)
【引言】動物當代思潮「荒野中的救贖:邁向原住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平衡」研討會,邀請九位來自原民權益、原民狩獵文化、動物權、野生動物保育及動物保護運動的專家學者發表演說,從動物權倫理、生態保育觀點到資源管理分析,來分析如何形成一種能夠考慮動物保護的原住民狩獵,除增進主流社會及原住民朋友對動物保護的理解外,也希望能貢獻更深入的觀點,使未來政府決策更為多元。
首先,向今天對於這個議題非常關心的各位朋友說聲,大家好。
我想先說明一下這個題目。什麼叫「正念場」呢?基本上是源自佛教的用語,是指佛教徒在修行時達到最高境界有八種方法、八種途徑,當中有一個叫做正念場,意思是說,必須要去除掉一些不真實的、不符合道理的一些雜念,如此才有辦法去領悟佛道,去思考正確的真理。在準備我擬處理的題目的過程,我一直嘗試地想釐清整個問題思考的脈絡,或者是問題的層次加以釐清。另外「正念場」這個詞,其實在日本比較常被使用,不過多數是用在流行術語上面,特別在歌詞當中,主要是意謂:「我要追求這個人,追求他的心,現在是我要獲得他的愛的一個關鍵時刻」。今天我在完成這個議題的準備過程當中,其實也覺得今天這場應該也是個關鍵時刻,因為這個議題難得有如此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被闡述與探討,或有來自動物保育的關懷,或來自於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的保障,因此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鍵時刻,就是由選舉新產生出來的總統正式出面向原住民族表示道歉,個人覺得總統代表政府道歉這是一個開啟,那怎麼樣進一步銜接下去以及進一步去討論,就有它的重要性。
雖然我的題目叫做「.....正念場」,但不過是要跟各位說明那是我心境的描述,只是我個人正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嘗試這樣去釐清,也同時嘗試地幫助我自己去釐清議題而已。此外,原民狩獵,我姑且不稱作「權」,原民狩獵這樣一個現象跟動物保育這樣一個訴求,對於這兩個議題碰撞在一起之後所延伸的問題,我自己嘗試釐清出來的一條思考的道路。
首先,我們要去釐清一條路的時候,必須要先做幾件事情,第一個就是「爭點」以及「範圍」的界定,亦即議題跟範圍的界定。
-
爭點範圍的界定
-
動物保護vs動物保育
我個人無意要冒犯主辦單位,但主辦單位用了「動物保護」這個概念,儘管「動物保護」這個概念並非跟「動物保育」是互相排斥的,但是起碼在法言法,從個人的法律專業角度而言,動物保護相應的是《動物保護法》,可是今天比較聚焦的應該是討論動物保育的問題,並對應到《動物保育法》。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前者基本上是以個體保護為中心,並放置在環境倫理或是動物倫理的脈絡之下去作討論的;相對於此,動物保育的話,是涉及物種保護的問題,任何的物種應該是連同牠的棲地一併被保護,否則就叫做動物園。即如前幾場精闢的演講裡面提到的荒野或者是說自然環境,這種情況之下,與其說是物種保護,還不如說我們要去做棲地保護。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涉及到這樣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跟「土地」的連結性會非常高,進而涉及到所謂「傳統領域」這個問題。「動物保護」與「動物保育」兩者之間,個人認為並沒有互斥,甚至可以這樣說,當我們在談論動物保護時,而且是從動物倫理的角度出發,或者將這議題侷限在《動物保護法》範圍內來討論的話,那未必會直接碰觸到「動物保育」。但相對來講,個人認為後者是包含前者,也就是說,即便是在為狩獵行為,縱使是法所容許可去狩獵動物,但是並不代表可以把牠當作一般的「物」,如同桌子或椅子一般沒有生命的物來對待,因為牠是有生命的一個物體,甚至稱牠是一個物體都是在貶低牠們的地位。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即便個人認為說今天這個場域應該是在談論「動物保育」,然而相對的,縱使狩獵受到法的承認或尊重(這邊所說法的層次不是只有侷限於法律這個層次,容後說明)也並非意謂,屬於個體保護性質或是動物倫理脈絡的動物保護是可以被忽略。然而由於時間有限,底下仍先聚焦在物種跟棲地保育的問題點上面來討論與原住民族狩獵行為的問題。
-
《原基法》第19條與《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的合致性
最近看到很多相關的報導,尤其幾個月來的相關報導都在探討《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野保法)這兩部法的關係,在法律上這涉及所謂「合致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二者在解釋與適用上如何契合,如何去透過解釋或是適用讓二者不會彼此衝突、不會互相矛盾。相關報導提到,《原基法》第19條明明在條文中有提到「自用」目的之狩獵,而《原基法》又屬於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在法律上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這條文當中既然有包含「自用」目的的話,憑什麼《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可以排除「自用」目的?《野保法》是不是太侷限了,為什麼只有傳統文化跟祭儀才可以為捕獵、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為什麼沒有自用?之前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主要多集中在法律條文解釋的技術層次,也就是法條發生競合時,應該如何解釋的這樣一個層次,然而前述問題的解答,個人以為若單純看這兩部法律中的這兩個條文,即使看穿、看破紙張也看不到答案。因為相對來講,個人覺得當中隱含很多矛盾的地方,應該先予釐清。
首先,儘管《原基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但如果沒有《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那麼《原基法》前述這一條規定是空洞的,只有宣示的作用。換句話說,這個條文雖然說依法可以從事這些行為,可是事實上仍必須找到一個特別的規定去讓原住民族可以為這些行為,所以《原基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所擬保障的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於是就連接到《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原基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實際來看好像是一個假象,但個人認為在法律的層次這是一個宣示性的意義,不能說完全空泛。再來就是立法技術上面很奇怪、充滿弔詭的地方,《原基法》都已經規定依其他法律可以為這些行為了,為何又在第二項規定又限制「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也就是以舊的一部法律去限制其他立法在後的法律。也就是說,如果立法者透過《野保法》第21-1條的增訂,訂定更廣的狩獵範圍與目的的話,我們再回到《原基法》第19條第2項的規定來看時,它就說「不行,你不可以這麼廣,因為你只有這三個目的」,這在立法上面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特例。我不能說瑕疵,只是覺得莫名其妙,這等同是以舊的民主意志去對於新的民主意志展現加以限制。
第二個問題,若從這兩部法的「時序」來看的話,就會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為何這條文在解釋上必定排除掉非商業自用?其實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因為這個條文是在《野保法》通過之後第一次修法的時候增訂進來的條文,也就是在1994年。當時條文提到,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這兩個目的,原住民族可以去補獵、宰殺、利用之行為。這邊所謂傳統文化,這邊我就不解,為何必然自用或營利自用?如果傳統文化裡面它如果本身就有包含捕獵野生動物自用,那本來就已經被包含傳統文化裡面的行為概念,又何須特別明文規定才能算數?也就是說,這個條文本來就沒有必然被限制不包含自用。就傳統文化而言,每個民族都不一樣,譬如說在野外看到一條百步蛇,在不同的民族之間,接下來事情的發展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族群在土地利用,或者是在狩獵野生動物這一塊,傳統文化所包含的意義可能是有差異的,有的可能對野生動物捕獵純粹是用在祭典,有的可能是用在跟祭典無關的自用。抱歉說一句台語來比喻,就是所謂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所以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吃」並不是僅限定食用,例如捕獵完後,把牠用鹽巴醃一醃可以吃一整年,不是這樣的。這裡所謂的「吃」是一種依賴的關係,也就是還包含用來交易。所以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從《野保法》這個條文來解釋,為什麼會就等於是排除掉「非商業自用」、「非營利自用」,甚至是「營利自用」,如果在某一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裏面,這些行為本來就包含在裡面的話,為什麼會不受《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的保障,其實這一點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
許可制vs報備制
《原基法》第19條以及《野保法》第21-1條之間,被提出討論的除了有關非商業自用是不是應該被納進來之外,另外一個重點是《野保法》第21-1條第2項的條文是使用所謂的「核准」的控管機制。「核准」在法律上就是所謂的許可制,於是就會有人提到說,在這種情況下,好像我們的文化的認同或是我們的主體性認同,必須要讓他民族來肯定、來確認,那這不是對我的主體性的踐踏嗎?所以是不是應該要讓一步,不要那麼霸道,應該要用「報備」的機制。從支持許可制的角度會覺得說,採取報備制主管機關沒有辦法事先審核,所以到時候野生動物族群數量減少發生失控的情形怎麼辦?所以這就是以有效管制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情。如果支持報備制的話就會覺得說,這才是一種相對尊重跟信任。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其實報備也是不夠尊重跟信任,因為報備跟許可都是由上而下去看這件事情,而不是一種平起平坐、不是一個夥伴關係,更不是一個共管機制。即便今天要談共管機制,但是報備不過是管制強度低一點的控管機制,到底仍不是一個共管機制的產物。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許可不夠好,然而報備真的夠理想嗎?報備真的有符合解決這個問題的本質嗎?當然我們要先確定問題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個就是等一下我要去做的界定。
-
傳統文化、祭儀到非營利自用
剛才提到《野保法》第21-1條規定中的傳統文化跟祭儀是不是就沒有包涵非營利自用?因此我們要把這個狩獵目的加以擴張,擴張到這個非營利自用這一塊。其實這個問題的本質根本不是文字的問題,而是應該放在族群的層次去看待。因為從族群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那麼到底是包含非營利自用,問題本質是不是就應該連結到土地權的討論,從而使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權利更加完備、更加完整呢?還是說不是,我們只是針對社會弱勢透過立法放寬狩獵目的來予以補償,就是說部分原住民族沒辦法吃什麼山珍海味,而在病重的時候想要吃點懷念的口味等等這些,所以應該放寬限制。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可能就不一定是一個族群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是把這個問題放在土地權的脈絡去思考的話,那就是一個族群的問題。前述討論的問題本質,基本上若是對原住民族議題有充分熟悉的人,應該馬上就會銜接到「土地權」的議題討論。
-
原民狩獵於法上的意義
在談論這個議題之前,仍要去承認一個事情,我們從哪一個思考脈絡或者討論脈絡去找到那個根源,那我認為必須得承認殖民統治這件事情。我個人一直認為,我們這一塊土地的原住民族到目前為止還被殖民統治,但我也認為不僅是原住民族,假如統治者並不是以站在這個土地的主體去思考,相對於被統治者係以這一塊土地為主體在生活,或以此為中心建構其價值觀,那麼這樣的統治者就是殖民統治。
我認為原住民族其實到現在為止仍然是被殖民統治。在原住民族被殖民統治之下,在近代我們經常會討論的事情就是,我們宣稱要回復他們的地位,或者是宣稱我們要去尊重他們,但是到底我們要以他們為主體,要去尊重他們的什麼主張呢?其實這是涉及到土地權的主張,什麼叫土地權呢?土地權是對於傳統領域的土地的一種掌控,還有土地上面自然資源的取用,那取用範圍當然就包含農林漁牧,因此狩獵就是在這樣一個脈絡之下被歸屬到土地權的範圍。從土地權出發,土地資源的控管,對原住民族的意義是什麼?它就是一個實現自我發展最必要的基礎,但是這句話隨著不同的時空還有不同的現狀會有所變化,也就是說,這個基礎、這樣的描述到底存不存在會隨著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原住民族,以及發展的現狀會有所差異。換句話說,可能在特定的時空之下,原住民族對土地的取用權可能會發生質變。亦即當多數群體已經不在傳統領域在上面生活,其生活方式與土地上面的資源管理,因有空間上的距離,導致其脈絡已不完整,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也許主張對於自然資源的取用權就不一定會成立。再來就是土地權跟民族自決權,這兩者被視為是原住民族基本的權利,即自決權跟土地權是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它是一個集體權。如果把土地權視為集體權,那從這樣脈絡所發展出來的一個狩獵當然也是一個集體權,這就是為何我把它理解為群體的權利而非個人的權利。
如果我們從殖民統治的角度去思考,而且也去承認殖民統治的事實,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承認之後要做什麼呢?承認的目的就是要反省!如果不想反省,那麼也不用去承認,因為承認、反省之後,就必須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對於這樣被殖民的對象,如果要給予尊重,要給予應有的尊重跟對待的話,其實這是涉及憲法高度的權利的問題,這不是只有透過法律來做調整就可以解決了。尤其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就必須考慮到歷史因素,從整個歷史脈絡來看的話,在外來政權(包含漢民族)還沒有來之前,原住民族本來就是在這裡生存。外來政權來了之後即採取壓抑原住民族的手段。當因時空變遷,我們非得要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則應該是立於國家的高度,對等的角度去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對於土地的管理或資源的利用有很多很多方法,我都不反對,但是我質疑的是為什麼在法律的層次上討論呢?這好像把原住民族當作是某一個縣市的人民、某一個社會的一個團體,但他並不是一個社會一般的團體。或許有人會無視這是一個民族、種族問題,可能視為是一個階級的一個問題,或是某一個地方的問題而已,但我不認為如此,我認為它是一個種族的問題,我認為它具有憲法高度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來看等同主張要返還曾經是原住民族的土地,但事實上確實有其困難之處,因此,在其他國家對原住民族與統治者之間的妥協,通常在現實考量之下,集中在剩餘的傳統土地以及剩餘傳統土地上方的資源得主張支配,亦即站在現實的狀況去討論這個問題。舉例來說,假如我要主張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領域,都必須以仍舊居住於我的傳統領域為前提,因此當生活的地點與範圍都已不在傳統領域之上,就無法主張集體的狩獵權。但相對地,原住民族也可以反駁,要求返還傳統領域上的土地,就此而言,我不會說完全不可行,但事實上難度比較高,因此較現實可行的是,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倘若原住民族仍然保有的傳統領域,即有必須要討論如何保障原住民族得以主張對於傳統領域上方的自然資源有支配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區分傳統領域與非傳統領域的狩獵。何謂非傳統領域的狩獵,舉例來說,這個民族雖然已經被遷徙到不是屬於自己族人原本的領域,但傳統經由口耳相傳,每年在特定的時間點他們做這樣的事情(例如狩獵行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涉及不是在傳統領域,可能是在其他族的領域上,或者是那個領域現在是有野生動物在上面,但它不是在傳統領域,也不是他族的,也就是一個沒有歸屬於任何族群的土地,或者可以說歸屬於國家的荒野的討論。首先來討論的是傳統領域的狩獵,想當然耳,第一個可以想到是與傳統文化以及祭儀有關,但為何源自於傳統領域的自然資源支配權的傳統文化裡面不能包含自用或交易呢?倘若在某些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包含狩獵自用與交易呢?為何不被包含在《野保法》裡面所指的傳統文化?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被限縮?除此之外,還有包含非基於傳統文化的交易,以及非基於傳統文化的自用。或許某些原住民族本來沒有這個文化,可是後來不知基於什麼原因,開始為狩獵行為,所以不是基於傳統文化。但值得進一步去問的是,應受到保障的狩獵行為一定要源自於傳統文化嗎?不一定!如果從狩獵權是從土地權延伸出來的脈絡來看的話,那麼在我對這個土地有資源的取用權的情況之下,原本我們對於這個土地上面的野生動物我們沒有捕獵,可是現在基於我需要、自用也好、交易也好,尤其是基於自用,於這種情況之下,所以我去交易、我去自用,即便是這種情況也是從土地權延伸而來的權利。所以我們必須要體系性地去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其實狩獵行為有些是源自於如同《野保法》裡中所謂的傳統文化或祭儀,但是也有可能並不是。即便不是源自土地權的情況之下,也並不是說既然不受到《野保法》特別的保障,那麼就不用特別去理會原住民族狩獵的問題。其實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它的行為目的是多樣化,甚至具流動性的。事實上狩獵行為背後的溯源與目的性會流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讓原住民族狩獵行為更加多樣化,其實這些多樣化的行為表現都有它存在的正當性、或者有它的淵源,而且又具有流動性,因此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呈現的態樣是複雜的。可是當我們若回頭檢視《野保法》第21-1條文時,其法律條文真的能夠乘載那麼多法律的功能嗎?真的有顧慮到狩獵行為前述的多樣化意涵嗎?我個人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
拉丁美洲原民自治權進展的對照
我發現,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與其主流社會的國家政權之間的發展與台灣有其相似之處。我個人認為,原住民族是從明鄭時期起迄今都一直被統治、殖民,如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一樣一直被殖民,而其整體發展的過程亦相似。我簡單說明拉丁美洲原民自治權進展三階段,首先從起初承認原住民族自治,可是原住民與統治者並非平起平坐,換句話說,原住民族是化外之民。其次,統治者把原住民族視為國民,乍看之下原住民族與其他的國民擁有相同的權利,但問題是在這樣子的法律之下,根本無視於原住民族與主流社群在文化、在社會以及在經濟發展上的差異性,所以導致即便原住民族被當作是國民,但是本質上的差異性沒有在法律上被考慮到,而造成事實上的排擠。然而,從1985年以後,中南美洲這些國家,漸漸地透過憲法去肯定對方,最重要的表現是原住民族是政權多元化的一環、一部分,這些國家不是用法律來處理這件事情,而是從憲法的角度去確定。這樣最主要的意義即是原住民族的自治權跟國家統治權,是放在同一個層次的。值得我們進一步去問的是,中南美洲這些願意從憲法層次與原住民族去建立自治權關係的國家,問題真的處理得很好嗎?用一句流行話,基本上是呈現出所謂「憲法以上法律未滿」,什麼意思呢?他們在憲法上面確實有這樣的規範,可是事實上,充其量只是去確立了自治權具有憲法層次的地位,也就是國家透過憲法去承認原住民族的自治權與國家政權是一種共享關係,也就是是一個國家政權多元化的表現,可是進一步的細緻的規定呢?其實目前的狀況還是空洞的。
-
原民狩獵於法上討論層次
最後再補充說明一下,我個人認為應該去區分傳統領域與非傳統領域,如果傳統領域之上的狩獵行為,應該被認為是從土地權發展、推演而來的,因此如何去界定合理行使對話是一個國家層級的對話,相關法律文件的位階應該是憲法層次的法律文件。所以反過來講就是,如果我們要處理的狩獵權具有這樣的本質的話,透過一個農政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組織,透過一個僅是法律層次的《野保法》來處理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已經把整個處理的層次拉低了。這麼低的層次,基本上,我不覺得真的有處理到問題,甚至有可能將一些隱藏在背後的一些主體踐踏與不尊重的情緒全部都翻出來,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只會更複雜,絕對不會更單純。
至於非傳統領域的狩獵的話,我認為就是屬於比較低層次的問題,甚至就是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授權透過法規命令即可處理的問題。所以個人認為說《野保法》第21-1條充其量只適合處理這樣的問題。相反地,若是涉及傳統領域的狩獵行為,我個人不認為,也不支持僅透過農政主管機關或者是以《野保法》來處理。另外,我個人也贊同尊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並不代表其如何自主管理土地,他民族或國家權利毫無置喙餘地。因為,退萬步而言,原住民族也是需要透過利用這一塊土地的資源,永續地在生存下去。此外,基於生態系統的相互影響與完整性,對於傳統領域自然資源的利用亦往往必然地會影響到其他民族的生存條件。因此,當然無法在此所謂的土地權跟主流民族處於毫不相干的關係。《野保法》的立法目的是什麼?個人覺得《野保法》的目的是在實踐一個國家保護義務,國家保護什麼?國家保護物種,並藉此來保護這一塊土地的人民生存。但這樣的立法目的是誰提出的?這個想法是主流民族所提出的物種保護思想,主流民族認同物種保護應該是國家的任務。然而,土地權一定會跟物種保護相對立、相矛盾嗎?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首先,若涉及傳統領域或土地權的討論時,這同時是涉及所謂自治範圍的界定,以及自主管理機制的建立,除了個人先前提到認為這個議題應該被提升到憲法的層次,或相當於憲法的層次之外,而且在這個層次去討論與協商如何平衡傳統領域自主管理與他民族的自然生存條件。至於若是非傳統領域的狩獵行為,則並非是從土地權所延伸出來的,因此即涉及主流民族的物種保護面向訴求,並透過國家保護義務的履行去限制「人民」的狩獵行為。即便是如此,仍應去考慮原住民族應受到的實質平等對待以及比例原則。就前者而言,就是族群的差異上必須被考慮到相關的生活脈絡、社會地位,否則極有可能轉變為一種以法律包裝的主流民族對少數民族的迫害。
再者,即是符合比例原則的法律拘束,當我們去提及何種物種應被保育,其實是科學問題,所以若要對於原住民族也好,或一般民眾的行為自由來做約束、做管制,則必須要充分說明法律拘束的正當性。也就是必須去針對各種物種的數量與現狀建立資料庫,必須要對於物種的現狀確實掌握,否則以純粹臆測的狀況對於人民行為予以拘束是欠缺正當性的。
-
結論
總統代表國家或代表主流社會?我個人可以接受她是代表主流社會,因此她對原住民族的道歉,我認為她把對原住民道歉的意涵以及整體的議題提升到國家的層次,但是後續呢?我個人認為是「誠意以上,憲法未滿」。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應該是誠意之後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做法?我選擇相信這部分也許總統府方面還在思考當中。但我認為應該完整被討論的問題不應該僅是狩獵,而應該是狩獵的根源─土地權。該土地權議題的本質涉及到憲法位階的問題討論,也是相關爭議問題的根源,所以應該去面對這個問題。今天在座也有很多人談到部落法人,這邊要強調的是,部落法人的討論應該是建立在一個國家政權共享的基礎,或者國家政權多元化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然而我看到不少討論竟然是放在與農田水利會公法人的比較去討論這個議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是在法律底下去談論的問題,壓根都沒有涉及到所謂的國家政權多元化的問題,所以我個人認為那是一個錯誤的類比。對此,我們應該談論的是,怎麼樣用一個協議的方式讓國家政權多元化,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要去思考如何把原住民狩獵議題的討論從《野保法》與《原基法》當中釋放,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原基法》再怎麼樣修法,就僅是法律而已,自始至終沒有辦法把一些應該放在國家層次去討論、平起平坐去討論的事情做一個適當處理。
最後,我希望這個問題的討論或許可以嘗試從資源共管的角度來思考。其次,要如何使良性的共管機制能被確保?個人認為不管是許可制或是報備制,皆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或許可以嘗試著用契約的方式。或許有人會擔心契約可靠嗎?我個人則認為不要忽略契約的作用,特別是公法性質的契約還是有一些在特殊的狀況發生時,為了確保公益可以讓公權力進場的機制。只不過是法律關係確立的一開始,仍先以平起平坐、用協商、用討論的方式來討論相關的權利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