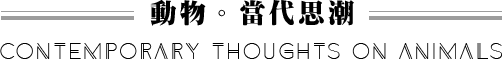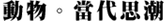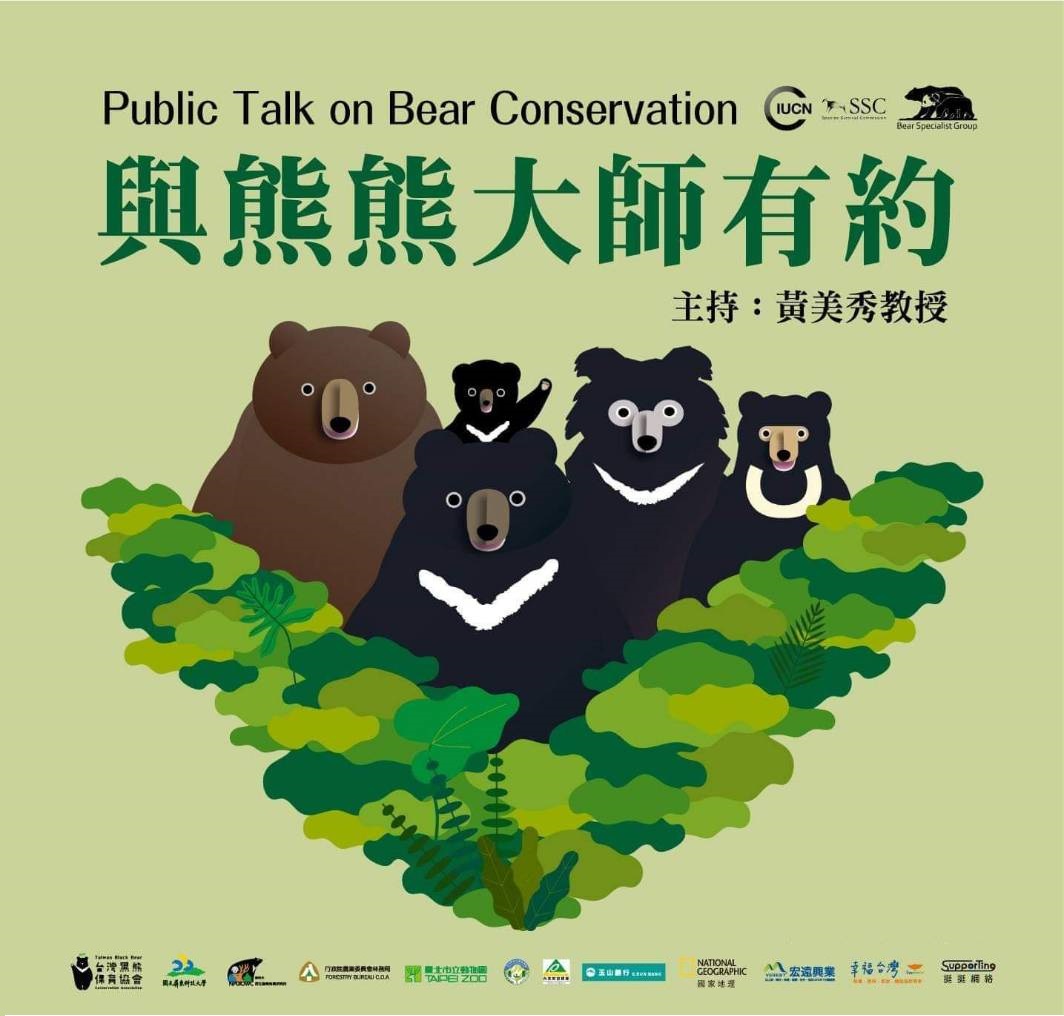主辦單位:台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動物當代思潮、關懷生命協會(依筆劃排序)
吳宗憲: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張卉君老師,請卉君老師今天來分享過去在做生態議題的政策倡議上面的經驗。卉君老師之前是參與了一些不同的環境運動的組織,在2005年開始到了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黑潮)。黑潮基金會其實非常有名,大概二十幾年前我就知道了,然後2014年到2020年之間卉君老師其實是擔任執行長。黑潮也做非常多的倡議,包括對一般民眾的保育觀念,這可能是一種社會的倡議,二方面可能是跟政府相關的倡議,經驗非常多。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相信會碰到很多正向,但相對一定也有很多負向的情緒或者是經驗,我們都很希望能夠藉由今天的機會,請卉君老師跟我們稍微來談一些問題。
我想我們在進到所謂的正式議題之前,我想請卉君老師說明一下,在過去這麼多年的就業、工作經驗裡面,怎麼去啟發、怎麼開始有政策倡議的想法?是從哪裡開始學習?比如生活經驗?哪裡開始產生這樣的種子?請卉君老師解釋一下。
張卉君:好。首先也很謝謝宗憲老師的邀請,老實說我今天要來分享自己在做議題的經驗,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還蠻誠惶誠恐,因為我真的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倡議的老手,然後也擔心自己經驗不足。其實在生命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學習,關於議題的這方面。當然對我來講,我覺得我會開始關注公共的領域,包含接觸社會運動,一個是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其實我覺得這個年代台灣其實有一種風氣,我們會開始關心公共的題目。更早之前我覺得是因為我的生命經驗,我自己本身就是921的災民,我在921地震之後,其實是有些受災的經驗,後來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在台文所的論文其實是在做報導文學。
在報導文學的領域裡面,我閱讀的比較多是跟苦難,或者說第一線的人民、動物相關的書寫,再來我又比較關心女性主義,女性對我來說也是被壓迫的一部分。所以後來我畢業之後,就還蠻直接的進入到第一份工作,剛好就是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對我影響非常深刻的鍾秀梅老師,他也是美濃人,他當時就有建議如果想要到災區做事的話,我可以做點什麼。所以當時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到災區去,9月份我就進到災區,我的田野調查是在新開,它是在六龜跟寶來之間的一個小聚落,也是小林村以外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聚落。我就到新開這邊來做災後的報導。
我的角色比較像是議題報導人,也就是災後報導,同時我也寫這些罹難者的故事,所以這樣比較像是實踐了我自己在做論文的時候,從一個研究者變成是一個真的進入田野的工作者。這個部分的關懷對我來講影響還蠻大的,埋下了一個種子,以至於到後來我在美濃也接觸到一個很重要的組織,叫做「美濃愛鄉協進會」。我在美濃愛鄉協進會工作了兩年,這兩年的工作期間其實讓我對於一個社區組織,卻在做非常重要的公民行動,而且他們是一個永不停止的一個社區公民行動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感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交工樂隊?
交工樂隊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樂隊,交工樂隊的主唱林生祥大哥,還有作詞人鍾永豐,其實他們都是當時美濃反水庫運動很重要的成員。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第一次聽到交工樂隊,因為我是一半的客家人,所以我聽到客家的一個樂團,你會感覺到很不一樣,它不是一個後搖或者不是一個輕鬆的樂團,而是你會發現歌曲裡帶著一種傾訴、帶著一種力量,它有它的沉重,可是它有它很積極的部分。那時候是我很模糊地去認識到,原來交工樂隊好像跟其他的樂團不太一樣,也讓我意識到音樂其實是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後來在我的教授引導之下,我加入了美濃愛鄉。其實從他們的反水庫運動的歷程──我沒有參與在過去,因為那真的是很長的一段歷史。反水庫運動是從1992年開始,美濃愛鄉協會1994年成立,所以我進去的時候已經比較後期了,他們前面反水庫運動最一開始的部分我沒有參與到──但是因為我在裡面工作,所以我會蠻常聽到他們在談到過去的事情,甚至因為水的問題一直沒有被解決,只要每次高雄缺水,水庫要不要蓋都會重新被提起。
所以我幾乎是覺得自己很幸運地參與在一個組織裡不同的階段,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在做公共議題的時候,從最早怎麼樣號召民眾,先讓民眾有這個意識開始,接下來怎麼去召集大家,怎麼去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跟我們的家鄉有關係,所以要關心,讓他們知道蓋一個水庫,你要淹掉一個黃蝶翠谷。我覺得美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是因為美濃它是一個客家村,而且主要是種菸葉,菸農其實在所有的農業裡面,我們都會說是比較像公務員,因為他們的收入相對來講是比較保障、穩定,所以美濃老一輩的菸農都很希望他們的子孫不要再做農了,早年老一輩的菸農會送子孫輩到美國或者是國外去留學。剛好在反水庫運動的時候,這批返鄉的知識份子回來了,他們回來之後要來保衛家鄉,我覺得那樣的精神、那個故事真的很勵志。
這批知識份子他們帶回來的工作方法,還有他們帶回來對話的對象,包含他們找國外的案例來談台灣要做水資源的時候,是否需要蓋一座水庫,甚至做很多生態的調查,讓大家知道生態的重要性。後來也來談所謂的里山倡議、有機農法,我們會聽到非常多,好像這幾年很流行的東西,其實在那時就已經提出,有很多是從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在發酵了。對我來講更重要就是,我看到了一個遍地開花的狀況,在這個運動它長達二十幾年的一個歷史的週期上,從最一開始他可能是來自一個事件,通常是很重要、緊急的事件,所以會召喚大家說有這件事情發生了,因此我們要來抗議,那就形成了議題。但是怎麼樣讓議題推進,或者說議題要怎麼樣可以走得更遠,或者說它有沒有辦法推進到民眾期待的方向,更甚是說環境、政策、民眾都贏,我覺得這是真的是需要長時間的一個觀察,我們才會知道。
我的啟蒙來自於原來這個運動做了這麼久到現在,我2010年開始進到美濃愛鄉,之前都已經過好多年了,可是現在我們還是在用不同方式,提出新的一些概念,像我們要做美濃自然國家公園,有沒有什麼方式是真的能夠保護黃蝶翠谷的生態不會被破壞的。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環境的議題,他要走這麼多年,而且時時刻刻都在依照時代的推進、政治的角力,然後它產生不同的面向,對我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很深刻的啟蒙,所以這也是我對於議題的認識。我就發現做議題不是真的只有上街去抗議,或者是去街頭衝,它在背後其實要做非常多的沙盤推演,甚至我們以前每次要做任何行動之前都要開好多的會前會。當時為了要保護黃蝶翠谷,所以美濃愛鄉協進會就創了一個美濃黃蝶季的活動,當年我是18屆美濃黃蝶季的總召,光是這個活動,我們籌備會是可以開到18籌,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的動能是捲動社區,你對話的對象包含溝通社區的居民,他們自己有沒有辦法做自然導覽,然後在過程當中他就能夠認同他的家鄉、認同保育這件事情,甚至他成為了一個會固定去做巡守的巡山人員、固定做生態紀錄的人員,更甚美濃還有外籍新娘的識字班。你會發現要讓整個農村的力量起來,他在各個層面都花了很大的力氣,而且很長期地去陪伴。所以我認為一個議題,你有沒有陪伴這件事是絕對看得到,而且他是非常需要經過考驗,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在做議題的時候很急,所以我們能考慮到的,或者是說能陪伴到的對象是很少的,反而有時候會產生很多的對話,或者是糾結和掙扎,「你保護了這個是不是其實傷害了另外一個?」可是事實上你們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才對。我常會覺得這就是我在參與議題的時候,一直都非常艱難的原因,因為不是每一個議題都有辦法像美濃的這個案例,走這麼久、這麼好,或者是說一直都有人持續在參與當中,反而很多的議題是像剛剛提到的「事件是突然來的」,我們必須處理它,所以我們沒有什麼方式,「這個方式是最好的嗎?」真的沒有答案,所以會產生蠻多爭議的。這大概是我當時的一個啟蒙。
吳宗憲:我覺得剛剛卉君老師講了好多重要的地方,也是我觀察到的現象。譬如一個議題要開始需要有政策窗,但是政策窗打開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他的運作不是順著我們、政府、或民間的意思,因為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因為當下情境底下的社會氛圍或者是文化的觀念,它就往某個方向去。在這過程裡如果不小心的話,很有可能是你剛剛說沒有辦法達成陪伴,更嚴重的是因為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而產生衝突傷害到另外一邊的人。但有時候我們把時間再拉長來看,當年我們傷害那些人,最後有可能回過頭來感激我們也不一定;或者說當年我們被他傷害的人,回過頭來我們想想他提出來的某些觀點,事後證明或許這是有意義的。我覺得剛剛講這些案例,你啟蒙的事件,我覺得不只是我,聽眾一定也都在這裡面有很多的啟發,我想後面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機會談到更多小細節。我們就進到下一個我自己也比較關心,而且是真正的我們在倡議時很核心的一件事情。
吳宗憲:
在2014年到2020年當中,你擔任黑潮執行長,不曉得你們怎麼去設定黑潮要設計、要參與的公共議題範疇?以及我們在這範疇界定完之後,可能就會有進到範疇內的這些議題,我們一定就要產生反應,在反應過程裡一定會有我們摸索出來的模式,不管是比較有用的、或者說是沒有用的,但是我們可能會產生一些曾經用過的模式,我想這部分可不可以麻煩您跟我們伙伴們做一個介紹。
張卉君:
我先簡述我們在海洋關注的議題面向。我常都會跟人家說我們真的是住海邊,所以管很寬,好像海相關的都跟我們有關,因為黑潮老實說是蠻早在台灣開始關注這些議題的。我們在1996年開始做尋鯨小組,是我們做鯨豚調查的前身,我們成立是1998年,可以想像20多年前台灣的環境運動才剛風起雲湧,那陸地上面的污染很多都要被關心了,更何況是海洋這一塊,所以當時黑潮可以算是少數專注在海洋這個主題的。我們去設定組織關心的主軸,希望透過海洋的關懷也能夠把一些海上的,比方說漁村的文化、海洋生態的保育等等,都能納進來。它其實是我們自己去以海洋為中心,如果說是用一個地理概念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從陸地跟海洋的交界處,包含像海岸、堤防、消波塊這些,或像過去的垃圾掩埋場都是蓋在海邊──就是從海邊發生的事、海岸開發等等,就是我們會去注意的,因為它其實就是陸地跟海洋的交接處,也是很直接的讓我們看到陸地的生活如何影響到海洋的過渡。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組織的歷史真的是非常的長,我們也在不同的時間點,因為不同的事件,做了不同的關懷和參與的模式。 最早我們其實比較多還是用文字的論述,我們會用比較軟性的方式,當時我們創會董事長是廖鴻基老師,他也是個作家。廖老師他非常擅長用文字來去呈現他看到的部分,加上他又有討海人的經驗,所以當時我們跟聯合副刊合作,就寫了一系列的文章發表在聯合副刊上面,當時是叫做「黑潮觀點」。這個「黑潮觀點」就把我們所關心的事情通通都含納進來,像剛提到的因為有些棲地的破壞,像消波塊,到底什麼樣的功法是比較友善的?還有海邊的焚化爐、海岸開發的問題,到底海洋是可以被「山也BOT、海也BOT」的嗎?這些其實就是過去我們介入的一個方式,當時也會跟公部門有一些對話,但是早年因為環保署或做河川的營建署、河川局,他們都是比較屬於工程背景,所以老實說工程背景的主管機關,他們對於生態的這一塊……
吳宗憲:比較沒有這麼友善。
張卉君:我覺得是他們沒有想過,因為我覺得大家的學習背景很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工程就是施工品質好不好,他就不會去考慮生態的問題,所以過去因為這些很直接的環境衝突會造成非常多問題,比方說抗議、去政府部門前面開記者會罵人、寫文章罵人等等,當時處理河海交接的問題就蠻常有這樣的衝突發生。那再來就是漁業的部分,我們關懷的面向慢慢延伸到海上,我們真的是在1996年開始就是在做鯨豚調查,所以海洋反而會是我們常出沒的一個場域,這個我覺得也是黑潮跟其他在台灣做海洋保育,或者說關注海洋議題的團體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是真的比較常跟海洋接觸,我們工作的領域跟範疇就是在海上。
因為你要在海上,所以你跟海洋的生產者會有很直接的對話跟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麼關心漁業,因為一來在廖鴻基老師的那個年代,他就發現討海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漁業資源枯竭現象已經開始了,有很多過去傳統的友善漁法已經消失了,慢慢地我們開始用大型的機器來取代這些漁業。如果大家看過公視的戰浪,你就會發現鏢旗魚,像這種標示漁業的漁法,比較是目標精確然後去捕撈的這種方法、漁法已經慢慢地消失了,因為人力的部分,包含後來引進外籍勞工,那台灣的漁民本身也開始失業,所以造成漁業文化跟漁民的凋零。當今天工作者不再是本國人,不再是台灣的漁民,反而是用外來的勞力來替代的時候,相對來說船上或者是整個漁業所謂的「傳承」就會不見,文化也會不見,所以這部分一直都是我們很關心的一個點也是這樣。因此,基金會很早期就做了包含像漁村的文史記錄、踏查記錄,包含當時因為要蓋花蓮港,所以把整個鳥踏石漁村遷村,那個漁村就不見了,像這樣子的一個文史記錄,其實是我們早期蠻著力在做的事情,所以這個部分不只是科學調查,應該說這部分比較著重的反而是人文、文史,比較是質性研究的部分。
當然在討論漁具這塊,我們常常會聽到一些討海人說:「你們黑潮都是你們在保護海豚,我們的魚都被吃光了。」老實說是有一些鯨類,他們是會跟著在鉤的後面,尤其像是延繩釣,可能你會看到偽虎鯨跟在你後面,然後你拉上來之後就只剩下魚頭,這個狀況確實是有發生,但是那個量並不是像討海人理解的「我今天抓不到魚就是因為太多鯨豚所以沒有魚了」。我們為了要反駁這一點,我們決定去瞭解漁法,這件事其實就有助於去用比較科學、有依據的方法,去觀察其實用不同的漁法,有可能是趕盡殺絕、有可能是混獲,造成的漁業資源的消耗,甚至是比傳統的討海人,──他們認為都是海豚把魚吃掉了──這件事是我們想要回答的部分。
所以當時在漁業這塊,我們做了蠻多的記錄,包括走訪全台灣的漁港,去做了台灣當代魚的記錄,也就是調查現在有哪些魚、在什麼樣的季節出現、在什麼樣的地方、怎麼抓的,還有台灣現在用哪些漁法與其方法等等。所以我們基金會在漁業跟討海人的關係是蠻密切的,這也是我覺得我們在後來面對海洋產業跟生態保育問題時,我們會特別糾結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對於漁業或討海人的認識,我們知道這個產業,我們也有情感,所以我們會非常糾結。
除了漁業之外,我們老本行當然就是鯨豚保育。從最早鯨豚調查起家之後,開啟了我們長期做鯨豚記錄,這個調查其實也是因為拜賞鯨業的發展之賜,也就是說我們跟賞鯨業有一個合作關係,這個合作是我們可以有人上船去做鯨豚募集記錄。長期的野外調查記錄,老實說如果你真的要靠政府補助的話,每年是上百萬在燒,但是大家應該都知道台灣在保育這塊的經費永遠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海洋的更是,大家都不想把錢丟到海裡面,所以當時我覺得跟賞鯨業合作是一個蠻有趣,或者說蠻聰明的一個方法,我們等於是變成了有自己的方式可以去長期做調查。那也是因為人力的關係,賞鯨船業者其實覺得這是件很麻煩的事,我們上船能回饋他的,就是我們做解說員,我們認為做優質的解說對我們來講,很重要的目的是,我們認為船隻就是海洋的移動教室,我們有機會去做環境教育,不要說宣導,因為我覺得宣導很僵硬,可是對我們來說就是環境理念的傳達,然後帶著遊客或者觀光客出海之餘,能夠寓教於樂,也能夠讓我們談我們想要談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軟性的議題傳達方式。
老師有看到我寫的文章,主要就是我們在解說員的培訓課程中,會讓大家瞭解議題是什麼、我們在關心什麼、他們傳達的對象是誰,解說員傳達對象就會是社會大眾,尤其是對我們來講最好的軟性的傳達。在海上久了,我們做鯨豚長期的資源調查,也會去觀察賞鯨船對於鯨豚的衝擊和影響,畢竟賞鯨這件事還是有個載具,就是你的船隻。你看到鯨豚的時候,他畢竟還是個商業行為,所以不是每個船家他都有sense,或者說都有辦法好好的開船,因為他們會顧慮要出船的時間,或者是要讓客人看得到鯨豚、我要多開幾班船等各種商業考量,其實他都是有可能會影響到賞鯨的品質,還有對生物的衝擊。所以賞鯨規範的部分……其實這是一個很弔詭的事情,因為他這個活動是先開始,但是沒有這個法令,而是先有這個活動。所以我們才會很積極地希望,是不是能夠在賞鯨這一塊上面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範,所以賞鯨規範也是我們關注的題目。
再來就是非法捕獵的行為,像大家雖然知道就是鯨豚在1990年後被列為保育類動物,受《野保法》保護,不能獵殺和騷擾牠,但事實上我們還是常常發現有獵捕海豚的行為,所以像這種非法獵殺,如果剛好我們在海上、賞鯨船有看到漁船做這件事,我們會遇到的案件。這些大概是我們在鯨豚的關懷,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圈養議題。你如果是以鯨豚保育的角度來講,我們會覺得你長期在海上看這些自由自在的鯨豚,怎麼有辦法接受牠被關起來呢?你在海上看得到牠們整個家族、族群史以及動物行為──而且台灣真的是非常幸運,全世界80多種的鯨豚種類裡面,我們曾經在台灣的沿海目擊過就有30多種──,在生物的多樣性,還有野外行為的豐富程度上來說,我們都會覺得台灣根本不需要水族館啊!為什麼我們需要把動物抓起來,然後再做表演給人類看,然後還稱之為海洋教育?所以圈養也變成我們後來強力關注的事情。
接著就是海洋污染的範疇,範疇很大啊,包含海洋廢棄物,海洋廢棄物其實就是從陸地到海域,還有從國外或者是漁船上拋出來垃圾的海洋污染,也包含人為的廢水,像之前花蓮比較大家會常聽到的,中華紙漿場排放廢水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長期在關心的題目。所以總的來講,從地理的概念來看,從沿岸到海域,我們關心的就是棲地破壞、過漁混獲、鯨豚保育、海洋污染,這四大面向大概是我們組織多年來關注的議題。
這些議題當然也會透過各種方式傳達出去,包含剛剛提到寫文章是比較軟性的,我們比較擅長的是用教育的模式跟大眾溝通,或者透過講座去做倡議。比較直接的話包含我們會去和生產者對話,像漁民、討海人或者是中華紙漿廠,這些本身是製造污染者,或者他可能在產業裡面扮演生產者角色的對象,我們就會希望可以去溝通或瞭解為什麼會造成汙染。
再來我們會在一些開發案部分跟專家學者合作,畢竟我剛剛講了這麼多範疇,老實說我們基金會真的很小,我們的編制最多8個人,最少的時候就是1個人,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在遇到臨時事件,就是議題的時候,我們通常會找專家學者合作,畢竟有些專業領域並不是我們在短時間之內可以補齊的,除了去讀paper之外,我們也會跟一些學者溝通和串聯。我們也瞭解有些學者的研究經費是來自政府,所以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角色就會是私下的合作,因為只要他願意或他就他所學去講話,他的資料其實就能夠幫助我們去打開對話的可能性。對我來講,NGO比較是扮演這個角色。
有了這樣的資料後,我們就可以跟主政者或民意代表像立法委員溝通,或縣議員等。這個溝通比較會是推動法治的遊說,或是說我們是不是有機會請對方去處理這個事情,就去召集、討論、找相關人,他們等於能夠去召集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一起做法治化的討論。所以我們溝通的對象包含大眾消費者、產業業者、學者、專家、主政者跟民意代表,透過這樣的方式完成我們的工作。
吳宗憲:剛剛這樣聽完,我們可以知道黑潮真的是管很寬,範疇真的很多,包括從海洋生產、漁業生產、棲地保育、垃圾問題,甚至動物圈養的問題,其實都關係在裡面。我剛剛聽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黑潮運作了這麼多年,也思考到很多問題,其實必須是多面向一起解釋的,它不能夠只看單面相,而且這樣做事實上對組織也有效益,比如說在賞鯨船上我們做的不只是教育,我們還能夠觀察到船隻對於鯨豚的影響,還能夠收集到鯨豚相關的資料,像這樣的設計,我覺得是多年摸索下來非常好的模式。我也曾經上過船去聽過解說,我真的覺得整艘船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解說員。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我們為了要做倡議,我們額外地做了文化的調查,也做了海上的生態調查、科學的調查,文化以及歷史的瞭解也是必須要的,因為只有這樣子才能夠思考並做出一個全面性的規劃,能夠對於鯨豚有利、對於魚有利、對於漁民也有利。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黑潮在這麼多年的工作摸索之下,重要且全方位性的學習也是值得我們大家參考的地方。
吳宗憲:我接下來有兩個更進一步的問題。首先,過去在卉君老師的經驗裡,不曉得您有沒有特別關注到哪些是您覺得很好、很正向的案例,你覺得他在政策倡議的過程中,可能運用了很好的策略,以至於最後成功達成本來想要達成的目標?想請老師說明。
不過在說明之前,我想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心情,剛剛您提到跟學者合作的部分,我太有感受了。因為學者要做研究,他沒有辦法有資源,除非他這個學者本身家裡經濟狀況非常好,但是通常家境很好的人不會來當學者,當學者的人他通常是有理想,可是他又必須有政府資源的挹注,這個也造成某種程度上是負面的影響。當他在做批評的時候,他的確要思考到給他補助單位的面子,也的確我們在做某些倡議的時候,我們跟NGO團體會做一些私下的合作,把一些資訊提供給NGO,讓NGO能夠去做更進一步的倡議。我覺得這也很好,因為學者有他這樣的位置,他才能夠拿得到經費、取到資料,不然我覺得NGO跟政府之間鐵板一塊的狀態,可能更沒有資訊可以對話。所以我覺得剛剛卉君老師這樣講我是很有感觸的,「人在曹營心在漢」。
張卉君: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理解,因為我們常常會在一個事件的過程中,把人分成好人壞人,你是正方還是反方,但事實上我們都忘記了這個角色本身,他有他的專長、他的定位,也有他的限制。所以我覺得確實對我來說,在後來的議題,我就不會區分你是一個壞的或好的學者,我們常會質疑學者「為什麼在開會當下不說你要採反對立場?」很多學者就告訴你「我是依照我所知道的說話,我只告訴你我的研究是什麼,但是我並不會告訴你說這是不可以的、這是對或錯」,但他會給你建議。我理解之後,就懂得私下溝通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像在環差之前,我們都會去拜訪可能是環評委員的學者,我們還會去搜尋他的背景,大概知道他參與了哪些的案子,他的專長是什麼?那他在這個案子裡面的發言,他主要會怎麼說?這個東西都是有會議記錄的,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會在遇到我們真正真實的test的時候,我們就會去跟他做私下溝通,就是會去拜會他說:「老師我們想知道您對這個事情的的看法是怎麼樣?如果是以您的專業來講的話,這樣子的一個開發行為它有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您手邊有沒有類似的研究,是已經發表了的嗎?發表的話我們可以在哪邊找到?」
對我來講,我覺得那是非常寶貴的學習,就是你要知道每一個人的角色,包含你自己的角色。像我們剛剛講這麼多的對話對象,對我來說NGO就是一個打開對話可能性的角色,所以你才需要更靈活的知道哪些人的局限是什麼?我們要針對哪些人?我們分別要用什麼策略對待他們、跟他們聊,讓他們變成整件事情的一部分,而不是要求他跟你用同樣的角色在事件上說一樣的話。所以我覺得後來我們去做那張圖,其實也是想要讓大家瞭解每個人有不同的位置,我們必須去理解這件事情,我們才有辦法在議題上推進。
吳宗憲: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不管是跟學者,或是跟其他政府機關合作,都會有這種要替對方考慮到他的角色,透過這個方式去思考我們的策略。我想你們的經驗裡一定也有一樣的看法,就是即便是學者,他也有分很多不同領域。第一個,不同領域的學者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社會學領域跟自然科學研究本身就不一樣,自然科學領域裡可能因為研究範疇的關係,他對很多知識的看法、理解常常都不同,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互相學習,也是一定要克服的一個重點。我覺得這個是跟夥伴們很好的提醒,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換位思考跟綜合大家的想法這件事情也很重要。我就回過頭來跟卉君老師請教,您的經驗裡哪些比較正向的倡議活動,你覺得很讚許,它實際上用了好的策略,並且最後得到好的結果,請你分享一下。
張卉君:我就用我自己參與過的來跟大家分享好了。我想先聊一個是應該是在103年、104年參與的193拓寬。193縣道是在花蓮的境內,他是能夠貫穿整個花蓮南北向的一條縣道。它整條路非常長,可是對花蓮縣政府來說,它就有一個預定拓寬的計畫,當時他們的講法是為了疏解之後蘇花改的車流。我們看到很多環境案子為什麼會有爭議?其實它很早就被核定了,所以才會有一個環境差異影響評估需求。縣道193拓寬的案子其實是民國88年就已經有條件通過環評,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要減緩花蓮港出入貨運車流量的衝擊,那是第一個拓寬的理由。當時在有條件通過環評的情況下,是沒有施工的,當時沒有錢,後來發現好像也沒有真正那樣急迫的需求,反正在整個政經背景下這個案子沒有啟動,到了民國99年,它又動了起來。
當時是在一個新訂的七星潭風景特定區的計畫,縣府再重新啟動。啟動的時候,他們就把本來的訴求──拓寬計畫本來的原因是為了要減緩花蓮港的貨運車,到了99年時,他的目標就寫成「未來發展觀光遊憩需求」,到了103年,他真正要開始動工前夕,就來了一則新聞報導寫「縣道193要拓寬了!」我們當時是看到報紙才知道193要被拓寬了。當時他們的目標就是像剛剛講的,為了要配合蘇花改通車、減少交通壅塞,因此他們就向交通部申請了生活圈經費補助的計畫,這個是經費來源,然後做整個海岸的拓寬。可是我們剛剛講到,縣道193其實是非常長的,它是橫貫整個花蓮縣,它要拓寬的範疇主要是從193縣道的0K到22.5K,大概是22.5公里的長度,也就是北段。它的右側是很靠近海域的,它本身是保安林,保安林就有一個保護目的,它為了要保護裡面的農田和居住的人民,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止鹽害、風害很重要的存在。
在整個歷史中,是保安林先劃定,但後來縣道為什麼可以開發,這其實是眾說紛紜。那也是後來我們慢慢釐清年代的發展,發現管理機關一直有變動。所以到底這條路為什麼可以拓寬?後來的政策其實是讓193縣道以東變成保安林,但是以西是解編的,所以以西這邊等於是私有林地,就變成你可以看到這條路的拓寬背後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就是要海景第一排的開發。
所以前面講的包含蘇花改通車等等很多目的,其實都不是真的,所以當時我們開始介入的時候,是我們跟地球公民基金會花蓮辦公室的夥伴一起。在花蓮比較尷尬,因為我們真的是同溫層很厚,花蓮就是一個居住的密度比較分散,在市區比較緊密,關心環境的團體也就是固定的,像荒野、花蓮環保聯盟鍾寶珠會長,再來就是黑潮,地球公民基金會其實是比較晚,他們比我們晚大概10年才來到花蓮設立辦公室。這些團體就紛紛注意到拓寬方案的事情,其實我們剛剛講在所有的大型開發裡面,193的開發老實說他不是一個很大範圍的開發,它的長度是22.5公里而已。可是事實上它影響到對我們很重要的保安林,這其實是我們過去做活動,還有很多花蓮人在生命經驗當中很重要的一段風景,而且我們可以說他是花蓮境內最靠近海邊的一大段防風林。
當時我們想要開始介入這個議題時,我們先讓民眾知道這件事,因為太多人不知道要拓寬了,連環保團體知道都是從新聞報導看到,當時我們知道這個計劃因為有經費了,所以已經準備要動工了,甚至環差會議也是想要草率通過。不過環差會議還是有一個年限,因為太久沒有動工,所以它還是必須要經過這個程序,後來我們利用了這個,去要求我們需要有環境影響評估裡面的項目,包含生態的衝擊會有什麼,縣府開發的路段裡面,尤其是北段的保安林,照理來說是不得解編的,原先拓寬的範圍劃定是要解編部分保安林,所以我們本來的策略是希望透過北段保安林不得解編來保住整個22.5公里都不准拓寬,來擋住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環差會議上,要求縣府說我們要現勘,要求發錢的單位來聽民眾意見,當時公路總局還有相關的工程單位都因為民眾的要求,所以他們就辦了現場勘查。我們也很積極參與,參與時我們希望不要像之前──花蓮的環保團體有個傷痛是在蘇花道路上。當時要開蘇花高速公路這件事,某個程度來講,其實造成在花蓮做公共議題的環保團體與在地民眾之間非常大的撕裂。因為花蓮真的是被視為後山太久,大家都很想要後山有發展,如果一條路的開發能夠帶來發展,有什麼不好?大家都這樣想,所以一般民眾當然希望有更多人潮來花蓮,開這條路有什麼不可以?可是對於環保團體或關心生態的朋友來講,大家當然會擔心這條公路的範圍那麼長,會通過哪些山、會影響到哪些生態的問題?當時的爭吵其實是非常激烈的,同時很強烈的對立也產生了。
當然過去有些年輕人,當時他們也是有這個概念的,我有幾個在那時在那邊工作的夥伴,後來他們還是有回到花東辦公室,可是大家講起蘇花高這件事時,真的會覺得是很強烈的運動傷害。蘇花高那時的策略是讓更多花蓮以外的人知道這是公共的事情,所以當時像藝文人士、導演等,他們都在台北公開發言反對蘇花高。可是對於在地民眾來講,就會覺得「我們不要永遠當次等公民,這是你們臺北人的想像,那不是我們花蓮人的想像」,這時候就產生了地域性強烈的對立。所以為了不要重複當時的狀況,我們在193拓寬議題上,就把外面的聲音延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我們先讓大眾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包含我們先從軟性的活動開始,我們去會做一些保安林的教育,去問大家「你認識保安林嗎?」沒聽過的話,就會繼續追問「你知道黑森林吧?黑森林其實是北段的保安林」在花蓮的人小時候都這樣暱稱它,它正式的名稱叫德燕濱海植物園,但是因為它都是防風林,長得很茂盛,所以大家都叫它黑森林。我們後來才在過程中發現,這條保安林其實是很多花蓮人約會的地方,所以就會有民眾想到,「我以前在那邊把到我太太的」,記憶就回來了,所以今天當他們回朔到知道這個環境要被改變的時候,其實大家的情感衝擊就會很快上來,就會發現「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我覺得民眾第一個反應都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也讓我們核實了一件事,就是「知道這件事情」是初始階段最需要傳達的部分,因為當人知道了之後,他才有選擇這件事情發生與否的可能。假設他知道即將發生這件事,他也知道生態會受衝擊,但他還是選擇要這樣,那是一回事;可是如果在他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他被迫選擇,甚至環境不知不覺被改變了,我覺得那就是比較強烈的衝擊。在花蓮也是常常是這樣,因為我們是花蓮國,我們有富國王嘛,在過去政治勢力比較單一的時候,在花蓮其實很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所以193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新的嘗試,這麼多條路都在被開發,你看溝仔尾都被蓋起來變香榭大道,當時也很多人反對,可是後來運動沒有成功,還是被蓋成停車場。
193這件事情我們就覺得,我們要好好的、慢慢的來做,所以真的就是陪公子讀書,環評會議、環差會議、每一個鄉的公聽會我們都到,跟著這些環評委員一起讀報告書,我都覺得大家在做議題的時候要很認真在做功課,我覺得我念研究所都沒有讀那麼多報告書,但就在做這件事情上,你反而需要看跟環評委員看的東西一樣,而且你要看到他看不到的內容。所以我們在193的參與的過程裡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跟民眾溝通、表達,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尤其是辦活動這件事情,甚至是我們會分眾,我們還會辦一些保安林的晚上Party,透過有趣的活動,讓上班族下班之後,用紅外線觀察保安林裡的生態,也會有親子的尋寶遊戲等等,這些軟性的活動,讓大家重新連結對環境的感情,對我們來講那才是第一步。第一步連結起來之後,他才會在乎說這裡要被改變,同時我們也在做剛剛講的環評會議、環差會議,我們就去讀報告、去現場參與、登記發言,然後做很多的沙盤推演。這個案子開了9次環差會,這樣其實真的是很少見,連花蓮縣政府都沒想過這樣一小條路我們可以搞那麼久,可以開這麼多會,我們開了9次的環差會議嘛,每一次我們都開記者會。
針對這件事情真的搞好久,最後我們守住了保安林,因為在過程中,我們也跟林務局有了溝通,因為保安林是他們的業務,那我們一開始會假設林管處很快就讓步了,這條路就要被開發了,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我後來發現剛好林管處的處長,他當時快要退休了,他就覺得不要有那麼大爭議,所以他態度反而比較保守,他們沒有接受縣政府的壓力說這塊地就是要解編。後來換了新的處長跟局長,中央的局長變成林華慶,他提出一些像國土綠網這樣的概念,那對於保安林他也有新的政策,所以我真的覺得是天時地利人和,就剛好林務局的態度是在保育更加重視,所以他們後來選擇在環差會議上,以主管機關的角度發言說「保安林不得解編」。我還記得那時候承辦的小姐是拿著稿子,而且他聲音都在抖,真的是大家都在旁邊看,想知道他要說什麼。林務局的態度很重要,因為今天假設說他同意解編,我們就知道我們下一步的行動策略就是抗議,用比較激烈的手段,比方說我們就會質疑為什麼林政單位沒有盡忠職守;但是他同意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變成要思考我們怎麼去支持他。所以我就覺得說關係其實是有些不同,後續我們就跟他們有些接觸,一開始他們覺得NGO很兇,他們超害怕我們的。
處長有一次跟我們約場勘,我們到現場的時候,他因為上個行程耽誤了半小時,我臉超臭,可是我臉臭不是因為他遲到,是跟志工喬不攏。可是他來的時候他就覺得「是我的錯」,一直道歉,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對於NGO真的很害怕,後來他們承辦人員有次就問我們黑潮有多少人,我就說辦公室5個人。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也透漏出公部門跟NGO之間很大的鴻溝,公部門很擔心,因為他覺得他沒有辦法跟你溝通,他不知道怎麼跟你溝通,他也很怕他講錯話你馬上就罵他。NGO的罵當然就是會是用比較強烈的表達方式,我們可能用寫的或開記者會,這個輿論其實是會影響到這些公務人員。
我覺得這是過去的套路,然後造成了一種恐懼,讓彼此有很大的不信任,但是在193的案例中,我們後來跟林務局反而變成是合作關係,裡應外合。我後來就發現林務局的人員工作真的就是在做林務保育,他們比我們熟100倍森林的重要性,所以當我們跟他們請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談得很深入,而且人家真的不是白幹事。我還印象深刻,當時在現場有些對於環境會比較激動的的夥伴,他站起來就直接罵工務局長還是誰,說:「你們有沒有良心?這是後代子孫的財產,你有沒有良心啊?」當下那個人他很冷靜,抬起頭來跟他講說:「不是只有你有良心」他說,「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你有良心,我是按照我的工作職責來做事。」我覺得當下是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不能覺得別人都是壞人,就像剛剛談的,他其實就是換位思考的角色。所以我覺得在193的倡議裡面,後來雖然它還是拓寬了,但它採用了另外不影響保安林的路線,我們都說是在陪縣府補考,因為環差的報告一次又一次,我們每次都是提出很多的意見,他們每次就去補充資料。我們覺得最後沒有辦法去阻擋他,其實很重要是整個環評制度的問題,就是只能讓它過,但是你要怎麼讓它更好地過,然後怎麼樣避開你最在乎的部分。
那過程當中我們也有跟民眾訪談,這真的是光一小段路搞三年的參與,每次來都是人仰馬翻。我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民眾真的有這個意識了,我們有非常明確地感受到民眾對這件事情的關心,我們發現花蓮在地關心公共事務、關心開發哪個東西、哪條路又怎麼了、保安林有人丟垃圾了、保安林的樹被砍了等等,我們後來就變警察局,很多人就會來跟我們投訴。那個案例讓我們覺得成功的原因,應該不能夠說完全成功,可是讓我覺得是比較正向的一個原因,其實是在民眾的意識提升,跟我們是守住了保安林,甚至我們後續有了一些保安林延伸保護的計畫。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3的案例。
吳宗憲:
因為我教談判學,所以我覺得剛剛您講的案例是我們在做談判裡的一個很重要、可以用來做很好的示範,因為裡頭提到了好多實際上跟政府談判的重要的策略。有一本書《How to Negotiate with Government》,我覺得寫得很好,書中提了很多重要的因素,剛剛您都提到了,活生生就是在193的這個事件裡被運用出來。比如說我們在跟政府談判,因為我們是比較小的組織,很難跟政府做全面性的對抗,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小地方,且是戳下去政府會痛的,這個戳下去會痛的就是環差。雖然會議我們參與地很辛苦,但是相較於全面性的抗爭以及了解所有問題,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罩門」,我們要去跟政府互動,因為我們小,我們只能戳他的罩門。再來就是利用本來他定的程序,因為我們自己要創造一個新的程序去反攻很難,但是我們就用政府的程序來打他,這個時候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接著,我覺得一般民眾不瞭解但也很重要的,就是政府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他是因為各種不同目的而成立的部門,所以內部一定有他們的目標宗旨,如果我們能夠知道他們組織內部的衝突,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製造他們互相之間的矛盾,也是一個可以達成目標的方法。
剛剛卉君老師講了很多地方,我覺得都非常有意義,我覺得夥伴應該都會得到很多的幫助。
最後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蘇花高的負面教訓是我們讓外面的聲音太快地大過內部的聲音,以至於我們想倡議的事情反而胎死腹中。但是我們回過頭來想另外一件事,就是台灣在好多的議題上,包括象牙的保育等等,這些議題反而是因為國外有壓力進來了,讓它能夠推動。我剛剛馬上把這兩件事情集結在一起,其實完全說得通,就是花蓮的民眾、乃至於全台灣的民眾,在這個權力或外力的概念下,他到底感受到的是什麼?
這常跟歷史有關係,因為花蓮人長久在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狀態下,他其實有一種一方面覺得被虧欠,二方面又覺得某方面確實沒有都市人那麼好,某種程度下是他討厭這些外面來的人,二方面又有一點自卑感在裡面,我覺得那種情緒交雜,反而讓外面的人要對他施壓的時候,他會有更大的壓力。可相對的,我們為什麼面對國外、美國的勢力,我們又這麼憋屈?我覺得那也是歷史的因素,因為我們一路從台獨運動,甚至國民政府到台灣來,其實非常仰賴國外的幫助,你才有辦法在冷戰的時候跟對方對抗。台灣民眾一樣會有一種自卑感,那種是面對西方人產生的自卑感,我覺得這樣講起來就非常有意思,文化跟歷史的因素其實在我們的遊說、談判、思考政治倡議的時候,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從您提的案例中,對我來講非常有啟發的一點。
張卉君:順著老師剛剛講到國外的經驗,其實我們在做一些環境運動的時候,常因為台灣的例子本身是面對本地的問題,參考的方式很多確實來自發展速度比較快的西方國家經驗。所以接下來我分享兩個案例,反圈養跟海洋廢棄物的議題,都是運用了西方的力量。
其實黑潮關注圈養議題已經蠻長一段時間,而且我們很信任且長期合作的對象,都是動物社會研究會(以下簡稱動社),我們跟他們在2006年開始針對海洋議題合作,也包含在2012年和關懷生命協會發起友善動物旅遊、拒絕動物戲謔的記者會;2013年我們跟動社做「期待海上相遇,要求立法禁止動物表演」的記者會;2015年時還做了一個大型的合作,一來是因為組織內部成員覺得,2006年做白鯨的相關議題,其實台灣民眾對於鯨豚,或者是動物表演的意識還沒有那麼強烈,後來時間拉長,後續又發生一系列展演動物的問題,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就跟動社討論可以怎麼樣在這個議題上再做更強力的發展。
那時剛好有一件事情,就是海生館有一隻白鯨死掉了。那次白鯨死亡之後,我們就做了比較強烈的介入。台灣現在有三個圈養海洋哺乳類動物,包含海獅、海豹還有鯨豚的場所,北部的野柳海洋世界、東部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南部有屏東海生館。在屏東海生館白鯨死亡案件發生之後,我們跟動社因為前面的合作的一些脈絡,所以就一起去發聲。當然因為黑潮主要是負責鯨豚相關議題,對於白鯨的狀況、當時在館內怎麼被飼養,甚至海生館做為一個教育機構,那些動物當時是透過教育的理由買進來的,可是動物卻是海景公司的,所以館方要怎麼照顧動物等這些事情我們責無旁貸,所以當時行動比較明確,像是要求館方讓我們可以去開會,去看動物為什麼會死亡。這些我覺得之所以能夠介入,有一個蠻重要的原因,就是海生館它擁有教育的角色。
當時因為白鯨的事件之後,再加上剛好2014年底我們跟浩然基金會申請到一筆經費,所以當時就規劃了一個行程,希望可以到英國拜訪WDC(國際鯨豚保育協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以下簡稱WDC)還有Born Free(生而自由基金會Born Free Foundation,以下簡稱Born Free)。歐盟當時有一個海哺動物的評鑑,我們也希望用他們的模式寫一份台灣的報告。當時參訪因為沒有很多錢,但是又希望去的每一個人都能發揮作用,畢竟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參訪,而是直接想要去遊說他們來關心台灣的海哺動物現況。
尤其是國際遊說這方面,動社就非常有經驗,所以我們就跟動社合作,像朱增宏他本身就跟這些組織有一些連接,所以就由他、玉敏、我們的董事鯨豚生態的專家蔡偉立,我們也邀請國內正在做鯨豚調查研究,比較年輕且同時是有現場經驗的學者余欣怡,另外還有基金會兩位成員,總共五個人去參訪。原本預計遊說的對象就是WDC、Born Free,去聊現在台灣的狀況如何,希望他們也可以來關心國內的狀況,同時也發現比台灣更嚴重的案例,像東南亞、中國大陸。其實在拜訪他們之前,我們有先去澳門號稱世界最大的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做考察,去看其中水族館動物的狀況。
考察回來之後,我們就發現真正的敵人在大陸。「太可怕了!」他們隨便一個館、一個池子,就是全台灣的動物、水族館的動物都在裡面,證明這不是只是在台灣這個池子裡幾隻動物的問題,而是背後整個圈養產業,它是全球性地運作。所以在過程當中其實也運用了一點政治的部分,就是我們是台灣,所以你看台灣跟中國有一個政治的關係,如果台灣能夠做到假設是全亞洲第一個零圈養國家的話,中國大陸是不是有可能也會有引導作用?我們期待可以用這種方式,讓國外的團體一起投入關注。剛好在拜訪他們的過程中,我們才知道其實這個聯盟也聘請了一個中國的研究員,秘密地在做中國的水族館調查。
我真的覺得時機點非常剛好,因為我們本來認為他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可是想不到他們也正開始。那年我們就希望台灣也加入,所以後來就組了一個中國鯨類保護聯盟,境內保護聯盟裡包含了像美國的Naomi博士,然後英國的WDC等等。我們本來要拜訪幾個很重要的單位,像香港的香港保育協會。基本上就是兩岸三地的人以外,再加上國際的專家,我們就邀請他們來台灣。首先就跟他們先組成了 CCA(中國鯨類保護聯盟China Cetacean Alliance,以下簡稱CCA),之後就開始擬定現在的目標,我們也發現其實台灣在動物福利或動物的教育方面,已經遠比中國大陸還要走得更前面了。
中國大陸的狀況其實非常的嚴重,而且方興未艾,他們才剛要蓋很多、很多的水族館,而且重點是我們發現他們是跟房地產發展是綁在一起的。這個事情在台灣跟在中國的策略就不能一樣,雖然要做的是跨國的事情,在CCA裡面其實做了蠻多討論跟經驗的分享。2015年時,我們還是希望──因為是台灣的團隊──透過遊說邀請他們來台灣,針對現況下台灣圈養動物的動物福利,或者討論這些動物應不應該被圈養等能有個進展。所以我們就請了他們來做台灣三館的現場調查,整個動物飼養的水池、表演的內容,我們請Naomi博士、中國的研究員跟香港的洪家耀博士一起,然後甚至去找館方的飼養員跟獸醫,去了解這三個場館裡面的配比是如何、動物的生活環境、水下噪音狀況等等。
這個就很困難了,因為這是商業機密,他們怎麼會願意告訴我們?比較成功的是屏東海生館,因為之前已經有溝通跟交手過了;後來是花蓮遠雄,他們是三個館裡比較新的,訓練方法和設備也比較新,他們認為自己做得很好,所以不怕別人看;野柳是最難溝通的,資訊也非常不透明,他是台灣第一個場館,從1981年就開始營運。總之溝通完之後, Naomi博士還寫了一份建議給他們,這個模式就是我們邀請專家做評鑑之後,會給園方建議,要怎麼樣可以讓你現在飼養的動物狀況更好。某種程度是出於善意,也是溝通,後來我們有非常多的互動,無論是檯面上或檯面下。那因為當時還是希望立法禁止動物表演,所以對他們來說就是「斷我們的生路」,所以遊說做了非常久,然後也換了好幾個立委,包括林淑芬立委、高天麟立委都有請他們遊說。這個部分主要是動社負責跟立委溝通,我們就持續跟產業界做互動。
後來我們還到中國去,就像剛剛前面講的,為什麼外國團體想要關心中國?像歐盟鯨豚被圈養的狀況已經很少,尤其像英國現在已經沒有關鯨豚的水族館了,那為什麼要關心這個產業?他們知道就算現在他們國家對待動物的狀況是OK的,可是全球的產業正在瘋狂的洗動,所以他們願意去關心。我們也拜訪了中國跟香港的組織,後來還去北京做了一個聯合記者會,那時候是知道中國這邊的概念還沒有那麼進步,他們沒有辦法用記者會呼籲的方式提出對政府的各種要求,所以當時我們在中國辦的是比較軟性、像沙龍一樣的活動,然後也邀請他們撰寫比照台灣的海哺動物評鑑報告,發表了一份中國的版本。
也因此,我們至少知道14個省份的水族館數量與現況,同時我們也分享台灣跟美國的狀況,後來又把這群學者帶到台灣來,這真是很像國際旅遊團,反正我們希望一次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後來我們就在台灣開了一個記者會,主題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今天談水族館的事情,講的其實是全球的產業,當時的策略就叫「交流旅遊、不要交流殘酷」,記者會也跟動社合作,邀請學者發言。
最後我們還辦了研討會,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這是 NGO自己辦的活動,地點選擇在台大,希望可以影響更多的人,當天還坐滿了。剛好我表妹是在學音樂的,所以活動最後他還演奏了一首箏的曲目,主題是「動物是自由的」。那次研討會我覺得也是很重要,我們提供從NGO的觀點來看,圈養動物牠們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各國狀況目前又是怎麼樣。除了這部分,我們也同步邀請合作多年的澳門足跡劇團。那年他們跟我說圈養這個題目其實有點難,而且他們在做偶劇的設計,然後要進到各個校園裡面巡演,讓孩子們知道這些動物不應該被關起來的生命教育問題。那為什麼會想要針對兒童?主要是因為爸爸、媽媽都會以為小孩想要去海洋公園,也會說是小孩要看,所以我們就針對小朋友下手,用藝術的方式來跟小朋友溝通,讓他們知道如果動物被關起來,牠可能會受到一些傷害,後來得到蠻正面的回饋。
學校的老師跟我們說,那一年的畢業旅行、戶外教學,就有小朋友提他們不要去海洋公園。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議題倡議的形式和對象有很多種,如果我們針對每一個議題相對應的情況,並且傳達給每個角色,其實就有機會彙集力量。當然在學校裡很重要的就是老師,雖然前面講去做偶劇的演出,然後小朋友也可以透過戲劇感受,可是怎麼讓學校老師理解生命教育是我們很重視的?所以當年我們也辦了教師研習營,帶老師了解為什麼我們認為去看動物表演是不好的。老師要有這樣的觀念,才會願意跟校長和主任溝通。我們後來發現老師是很弱勢的,學校裡需要被遊說的是有權勢的主任、校長,還有家長會長,他們覺得孩子要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就會選海洋公園。
學校對我們的質疑就會是「不然我們要去哪裡?」所以當時其實做研習營之外,我們還提出了一套教案,推薦給30所學校,讓他們來報名,然後戶外活動的規劃也有,比方去漁會,教他們認識漁獲和友善漁法,結合賞鯨、走漁港等等,用不同、安全的形式,提供消費者另外一個選擇,告訴他其實有不同的方法,不是只有去海洋公園才能夠讓學生學習。後來其實也有針對不得不去海洋公園的人──我們在做議題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老師或家長聽完倡議內容之後,就會帶著很大歉意跟我說:「我真的沒辦法,我家人真的很想去海洋公園,過年的時候我還是跟他們去了。」我就想跟他說,真的不用這麼有罪惡感。我覺得真的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心裡有這樣的概念,當然現況沒有辦法那麼快改變,但是要怎麼樣去影響身邊的人,其實不用那麼心急。我覺得我們會提供的方法是,假設你真的必須要到海洋公園去,就做海洋哺乳動物圈養觀察評鑑表。這份表是參考動社的Zoo check,也是當時跟英國取經來的,那我們就做了一個Aquarium check,就是海洋哺乳動物被圈養的時候,牠的哪些行為可以多了解、多觀察。所以我就跟不得不去海洋公園的人說,「你進去公園、去看表演不要覺得罪惡,因為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觀察者,把你所觀察的內容紀錄、傳達出來,同時也在扮演一個監督者。」
這是在圈養的議題上,基金會在做的事情。當然在阿河事件之後,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參與了動保法的修法,所以在《展演動物設置辦法》的幾次修法,就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所以後來這個議題我們覺得有階段性的成果,至少能夠讓現有的園內動物的動物福利比較能夠被討論跟照顧到,可是這個議題我還是有一些目標,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再有新的圈養個體出現。
台灣現在《野保法》其實已經可以比較不擔心有新的個體被捕捉進來,但是我們覺得接下來會討論的是人工繁殖,它是這個議題往下走的一個重點,因為如果有新的個體出現,這個產業就永遠不會結束,所以它必須是具有夕陽產業的情況下,我們才針對現有的動物做照護,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前提。
吳宗憲:我覺得剛剛卉君老師提的案例也非常有意思。在政治倡議過程中,我覺得幾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策略,比如在遊說國際組織來關心台灣議題的時候,剛剛講的相關經驗。的確,在做政治倡議的時候,其實很多組織他在思考目標的確會想到做這件事的效益,所以當我要說服他們來台灣,的確以台灣作為一個方向去影響中國大陸,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頭,我相信這個理由可能在當下是存在的,不過這個理由可能在未來、或是目前兩岸關係的狀況下就越來越越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在倡議過程中要思考問題,就是兩岸關係也影響到社會運動的倡議,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另外,怎麼去跟海生館做倡議的過程也提到了,是因為政府跟這個案件委外出去,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用的也是去製造公部門跟私部門之間的某些衝突,從中可以得到我們倡議的目標。我覺得最後卉君老師提到一個我覺得特別值得說的,就在我們系上。系上有老師跟我說「吳老師,我知道你是非常反對圈養海生館海洋動物,可是我這禮拜就要帶小朋友去,我先來跟你懺悔,我如果沒有跟你懺悔的話,我覺得過意不去。」我就跟他講你可以去幫忙做評估。
我覺得回過頭來,覺得面對沒有辦法改變的人,很好倡議的方法是借力使力,就是既然沒辦法改變,有沒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能夠讓他往正向的方向去前進?圈養動物這個議題,透過影響小孩子的方式,我看過好多案例是這麼做的,包括你們、動平會、動社會,甚至到學校關狗籠子,當然這樣子要取得學校跟父母親的同意,但是這樣的過程小孩就很有體會。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好的方法,但也提醒我一件事,就是每一個倡議都必須針對議題涉及到的利害關係人對症下藥,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吳宗憲:剛剛談了成功的案例,接下來想請卉君老師談談,在倡議過程裡可能運作沒那麼順利的案例,請卉君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張卉君:好,談到這就會非常沉重。我覺得做議題難免都會有運動傷害,像前面有討論到,通常事件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很急著想要去改變,或者是阻止,在這過程當中可能要非常快速地溝通,但是這個溝通往往會是帶有目的性的說服,他就比較不像前面講的長期觀察,或是用比較人類學的方式去蹲點,去認真地建立關係,所以其實真的會有一些案例是讓我們覺得處理得沒有那麼的周到的,然後也產生比較多的爭議和聲音。像我覺得漁業的部分應該是最近大家比較會看到的,漁業有個點是它有很明顯的利害關係人,它不像海洋廢棄物議題,基本上你談海廢其實不那麼困難,因為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它不是針對哪個族群,當然它也會有一些特定的族群,比方海洋的利用者,可是針對性沒有那麼強,其實你不會覺得那麼敏感。
可是像漁業,其實他就很明顯會針對這個行業的人。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在海洋資源上,它比陸地資源還要難被顧及,然後海洋研究也一向是非常少,對於海洋生物的瞭解,尤其是這些跨洋生物,有關的資料跟研究仍是相當大的空缺。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很難像前面的案例,或者陸地生物的案子一樣,有累積的資料可以作為遊說的後盾。所以我覺得自己在做漁業的議題時,一直都還蠻挫折的,就像我們跟討海人之間長期建立的一個關係,遇到衝突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這是非常難處理的事情。接下來要說的是個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應該也不能是失敗的案例,只是我在處理時很心急,做倡議的敏感度還沒有那麼高,所以我沒有特別意識到文章那樣寫,媒體會像鯊魚一樣聚集、嗜血。
當時是端午節,我們剛好在海上航行,發現了一隻被鏢刺的海豚。在海上時牠還是活著的,我們的船隻靠過去之後,漁船看見船隻靠近馬上就走了。我們只是覺得那隻海豚好像載浮載沉,所以就過去看,看完之後發現是活的,牠還沒有死亡,頭上就有一隻標槍。當下我們的解說員就想把牠帶回來,沒有想要採證,他只是想要救牠,另外一個就是假設牠真的快要死掉,至少要讓牠回來做標本。
後來就真的把牠帶回港,帶回港之後我們就放回到海巡那邊。海巡看到的時候,他們就只問我一句話:「你們有要報案嗎?」我就想一想,我:「當然要報案,這不是現行犯嗎?這是保育類動物,這隻鯨豚頭上就插著一隻鏢槍,而且牠死掉了。你還問我『你要不要報案』?」整個都很荒謬,因為他們可能也沒有想過,或是也沒有 sense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對我來講就會是,這隻海豚已經犧牲了生命,我要讓牠的犧牲是被知道的,大家以為保育類已經列為保育類好像就沒事了,事實上在海上的獵捕行為就是持續地在發生,今天只要有人需要,它就不會停止,只是會變成地下化。
所以我當下說要報案,接著我們就有跟比較信任的公視記者說這件事,當然他們也是聞風而至。那因為海豚死亡的時候,眼睛附近會有組織液流出來,我就拍了一張照片。當下事情處理完就去錄筆錄,記者採訪完後,我就在臉書上面寫了一小段〈海豚的眼淚〉的文章,這篇文章就被瘋傳,我當下沒有描述牠怎麼了,我只是因為今天發生了不幸的事件,然後用浪漫的筆法形容牠流下眼淚,牠生命的最後可能不知道看到什麼。然後這件事情就失控了。
我當下真的傻眼,我只能說我太小看社群網路的力量,一來不太瞭解媒體對這個東西如此嗜血, 對他們來講這是這麼好的題材,另外可能那幾天剛好也沒什麼新聞了,所以版面很大。整篇文章流傳地非常快,而且看到非常多酸言酸語,就有好多酸民就在臉書文章留言「漁民就是愚民」、「台灣就是鬼島」等等,我當下真的是覺得很心疼。
當然這是一個犯罪行為,這是非常地確定。可是當我看到那些留言的時候,我覺得「天啊我是不是做了一個引導風向的事情?」我這樣的描述對於事件是沒有幫助的。那些人其實不是不吃魚,大家也都是消費者,可是大眾會覺得這跟他無關,反而會去指責犯罪者,接下來你就會看到很多「是誰?」、「把漁民找出來」的言論。這個經驗讓我當下覺得「我很後悔」,即便我認為我只是在我的臉書上發言,但事實上臉書現在已經成為記者獵取媒材、拿去寫新聞的東西了,這同時也等於是公開發言。當時我真的沒有想到,當天晚上我馬上就熬夜寫了一篇〈漁人的眼淚〉,我想要反過來談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為什麼這隻保育類動物會被補殺、我們有沒有去想過這個討海人他的處境,當然對他來說一定是有利益的,可是他也知道那是違法行為,他為什麼鋌而走險做這件事情?我們是不是能夠再往後看?我常常會以「怎麼樣是結構性的東西」來看整個漁業的狀況,走私的行為背後的集團到底是哪些需求在供應?那些人到台西時,吃不吃這個東西?
我那時候的反省只想要提醒大家,今天發生這件事,每個人都有你的角色,如果我是一個完全沒有這些需求的國家,這個行為是不會發生的,大家有沒有辦法去做善的傳導?我們在乎這個事情,但是你要去傳遞的時候,不會是「動物好可憐」、「漁民好可惡」的想法,而是在這個關係中看到,漁民其實也是在社會底層,整個漁業是凋零的,漁民生活是有困境的?我們再用比較好的方式去傳達,所以當下我才寫了〈漁人的眼淚〉。那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在2010年的時候,我做了花蓮港討海人生命的口述歷史紀錄,那是一個兼具質性跟科學的研究。當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討海人做流刺網,流刺網在漁法裡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傷害性的,我當下真的沒有想到那個討海人自己是反對流刺網的。他很無奈的告訴我,他以前是漁會的幹部,他有說過政府不應該再發流刺網,那個傷害太大,但沒有人要聽他說話。他說:「我人微言輕,如果你們有辦法傳達出去的話,你們讀書人你們比較會,你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告訴別人?」
他居然跟我說,他認為花蓮應該要劃漁業保護區,有一個討海人自己覺得要有一個漁業保護區。他是使用者,他當然會知道怎麼樣使用會更友善,當然這是一個個案,不會每個漁民都有同樣的心情,可是我就寫了這個故事,讓大家知道其實生產者的的處境,並且希望不要弱弱相殘。這篇文章我希望可以去平衡上一篇,但這篇的反應大概只有前一篇的1/3,到這你會發現前面那個爭議已經燒出去了。這件事情給了我一個非常大的打擊,也知道之後處理議題時,要特別、特別小心。
所以後來我在處理鬼斧魟、巨口鯊的事情時,我自己都面臨到困境,也在試著找可以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當一種魚種很珍貴,就要被列為保育類,我們希望牠保育,通常會對外我不會直接講希望可以將其列為保育類,我會比較希望的是採取更積極的保育手段,就是無論政府或是科學家、研究者,都必須要往這個方向前進。這是我的期待,可是我不會馬上認為要列保育類。對我來講我擔心獵捕會變地下化,或其實這樣做根本沒有減少社會的對立,我不想要弱弱相殘,這些生物跟生產者本來就是一樣的,我們都認為「這個環境好,大家才能共榮,我們有一樣的目標,但是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翻攪的議題,用這個來跟大家分享。
吳宗憲:我覺得剛剛這個案例也非常精彩。當然用「精彩」這個字眼其實不大好,它也讓我們反省許多。我覺得我也呼應一下,剛剛您說引起酸民這件事情,其實我們研究政治的人是很關心這個的,甚至有些學問是專門去學怎麼讓輿論能夠很快地發酵出去,是有一些方法的,只是因為你剛好不小心用了那個方法。回過頭來想,跟這個案例有類似狀況的有很多,不要講動物,死刑犯、吸毒者,其實都是很類似的問題,我們只要寫一個故事,就很容易讓全部的箭都往那邊射去,結果大家都忘記回來思考,這個社會要付出的、整個系統應該去改變的問題,包括獄政、教育、輔導,毒品氾濫怎麼從學校管理的問題等。有時候是執政者透過這個方法讓弱勢者去弱弱相殘,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另外卉君老師剛剛提到,其實不要一味地去禁止,因為這樣做的話容易出現地下化的情況,所有的經濟行為因為有供需的問題,如果在政策上是一步到位就把它禁掉,有時候反而會得到反效果,所以回過頭來思考您剛剛的方案是可行性高一點的做法,然後漸進式地改革,這樣的方法可能更好一些。
其實在動物保護裡頭,尤其是經濟動物議題,包括蛋雞的系統、屠宰的問題,就是有好幾個議題都有類似的狀況。我們可以透過漸進式的方法,或者是我們通過另外的系統繞過去,比如建立一個新的蛋雞系統,還可以變成社會企業,或者它可能未必是社會企業,反正形成另外一套生產跟行銷的系統,然後慢慢地將民眾的習慣往那邊倒過去,但成本不能太高,或許能夠慢慢改變這件事。我相信這個也是漁業在做的事,怎麼讓永續海鮮能夠繼續,而不是就不去吃。
張卉君:因為大家關心的事情真的很多,會有不同的面向,但裡面都有它的共同性,我相信很多的倡議者都在痛苦、矛盾裡面,所以這個部分是很值得去思考。
吳宗憲:非常重要。我想就希望在最後這個時間請卉君老師再談談,在那麼多年倡議經驗中,是不是能夠歸納出一些你學到的心法,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可能是未來有志於做參與的夥伴都會面臨到的困境,我覺得可以提供他們做很好的參考,就麻煩您跟我們分享。
張卉君:我最後盡可能簡單做幾點分享。第一個是我自己在這幾年,不論是跟公部門的互動,包含林務局,2018年成立的海洋委員會,有海洋的專責機關成立之後,會發現整個政府的結構,還有公務人員的態度──他們也換了一批,也就是整個公務機關的人,還有基層的這些公務人員──我覺得都跟過去的方式不太一樣,那個不同呈現在態度,還有對話的方式。
所以我想第一個,他是一個鬆動的權力結構,他不再像過去好像作為民眾,我們只能接受公部門的法規指令,然後不服、覺得這很爛,接著去踢他的門,但他們也不理你,因為對他們來講「沒差,我撐過這兩天的新聞就好了」,所以事情也不會改變。過去很大的消耗是放在抗議這件事上,但抗議完、我們表達了聲音後,結果沒有改變,這是過去的溝通模式,也製造了蠻多的對立。現在我反而會覺得有些機會,這鬆動的權力結構讓我們有辦法在不同的角度倡議,或是更早去參與這些事情。
第二個是對話形式的多樣性,剛剛有講到非常多的溝通,每個不同的角色之間各自的立場。
吳宗憲:今天就是一種很好的對話。
張卉君:對,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對話形式。像在太陽花學運之後,也越來越多審議式民主這種對話的方式,它被創造出來了。所以我覺得對話形式的多樣性,是在溝通、遊說、訪談,然後怎麼透過互利的遊說做籌碼,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部分。
我後面寫了一句叫「做一個見縫插針的行動者」,其實來自於就是動社的師父給我的啟發,因為老實說我在做議題之前,我善惡分明,非常容易將人歸類,我會覺得「他跟我不一樣,他為什麼這樣講話?他是壞人。他就一定就是……」遇到這樣的狀況時,我就會覺得「我不要跟他講話,我不要跟他接觸」,因為不同立場。但是我後來發現,尤其是動物的議題,朱師父跟玉敏很常用同理心跟對方講話,所以我就在想「怎麼有辦法溝通呢?他不是壞人嗎?你怎麼有辦法這樣跟他講話?」可是你會發現,如果沒有這樣的身段,從對方的角度來談話,其實你根本改變不了現況,而是永遠在對立,所以後來我才理解到做議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為了要區分善惡嗎?
吳宗憲:是要讓自己的情緒能夠解放?還是讓自己的好能夠被凸顯出來?
張卉君:假設目的是要改變這件事情,就不會去講「你是壞人」、「你是好人」的分類,而是怎麼在不同角色裡面──我覺得見縫插針是一個靈活度,你怎麼去扮演你的角色,這個就是我覺得NGO工作者要的角色,我們的工作是打開對話的可能性,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是動社啟發我的心法。
第三個,議題通常起於一個急迫事件,但如果沒有從結構性的角度去瞭解的話,其實會很危險,所以我們會希望先從整體結構去瞭解之後,再決定階段性策略。
我覺得階段性策略很重要,如果你沒有先把時辰拉出來,或是沒有階段目標的話,就會覺得「我今天不做就沒有辦法達成,或者我今天只做這麼一點點,我失敗了」可是我認為階段性目標拉出來之後,才會知道我現在做到這邊是為了什麼,對於事件本身或倡議者本身,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和緩方式,同時他也讓你長期地去監督這個事情。倡議不會是短期的,我也認為倡議者也不應該只做短期的事,因為我們已經在改變事情、影響別人,如果只是短期的結果而不去看長期的話,對我而言那是一個不夠負責任的倡議。
所以對我來講階段性的策略行動擬定,它其實是一個負責任的方法。再來就是我常會提,「人」是在議題中我覺得很重要的考量點,並不是要從人的觀點出發,而是人從來都不在保育之外,因為這就是地球萬物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在談保育的時候,會覺得「人不見就算了」,當然這是玩笑話,可是其實回過頭來看,大家都知道動物牠們沒有問題,要處理的是人的問題。如果在考慮一件事情時,我們不去瞭解,就像不去溝通、對話,瞭解他們要的是什麼,我們能怎麼樣?不去跟人溝通的話,保育是沒有辦法往前走的。
吳宗憲:我們講得更那個一點,就算要人能夠漸漸消失,這也要他願意。
張卉君:也是,而且大家都需要環境,現在都會跟人家講是為了下一代,是為了地球好,才不是,地球根本不需要我們,是我們需要地球。
吳宗憲:我自己有觀察到環境跟動物保護運動很多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都是絕育者,都是覺得不需要有多餘人口。不好意思,請繼續。
張卉君:我也覺得是這樣。再來,我覺得參與議題的方式不是在門外吶喊,我們不是為了要表達情緒,而且現在對話的方式已經改變了,重要的是跟體制內願意改革的Key Person建立一個信任的基礎,共同合作,要找對人。當然這就是考驗你的功力和磨合的結果,你要觀察他,就像防風林這個案子,如果不是有這個議題,老實說我們跟林務局彼此還是不能理解對方的。可是如果今天有這個機會,或者看到有認真的公務人員,他也在改變怎麼去運用他的資源一點、一點地去撼動、鬆動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我都很佩服他們,就是所謂體制內的人還有學校的老師,因為對於體制外的倡議者來講,其實想要怎麼做都可以講得很快,因為我們很自由,但是對他們來說是在一個很有限的情況下堅持做他們認為對的事情。
吳宗憲:要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張卉君: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部分是大家要去理解的。再來,也因為今天有機會更提前能夠去參與對話跟政策的溝通,其實光我自己本身也參與了很多公部門單位的委員,這個委員的角色就符合「會議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NGO參與」的規定。為了要符合這個規定,公部門就會找一些跟利害相關的NGO一起談,我覺得進來談就會有助於大家瞭解彼此,同時也能夠把我們比較介意的事情,或者是過去得到不好的經驗,在這樣的平臺做討論。不過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你就會被認為是專家學者,但你夠專家嗎?
這件事情其實我一直很誠惶誠恐,我現在也快40歲了,可是以我的年紀來講,在黑潮這個比較老牌的組織中,我身為一個年輕的參與工作者,到底該怎麼撐起這個角色?我就必須更認真、更專業,因為既然你有機會被政府部門找去進入對話的時候,你要講什麼?今天政府找你了,可是你能講得出什麼東西來?這就考驗NGO的專業,所以我真的覺得NGO是越來越艱難,你的角色能夠發揮的機會變多了,可是相對來說你的專業性也要更加強。
最後一個,我覺得環境議題是很漫長的事情,動物議題也是。如果民眾的意識沒有起來的話,議題就不會成功。溝通對象這麼多元,大眾是非常大的一個基數,當今天大眾的意識起來時,政府部門才有信心覺得「民眾的反彈力道不會那麼強,我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商業部門、生產者這個部門,他也是聽消費者的,所以民眾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要經過這麼長期的醞釀,我們才有機會真正地在某些時間點見縫插針推動一些事情,所以我會認為議題其實是需要很長期的陪伴跟觀察,才有可能知道這個議題的方向到底是否正確、是否合宜,然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跟條件之下,要靈活地去審視、去檢視我們的倡議方式。這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我在這些年裡的學習跟從錯誤當中得到的一些心法。
吳宗憲:今天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相信各位夥伴如果能夠從頭看到尾──分三次看也ok──能夠看到後面的話,我覺得夥伴們很有福氣,第二個我自己一直以來是學公共政策的學生,我覺得卉君老師剛剛提的很多真的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很多觀念都是。雖然我跟卉君老師不熟,但是今天聽老師這樣講,我就覺得實在太合拍了,很多剛剛談的觀念,其實在課堂上,或者是在平常互動中,我都有跟我的學生分享到這些。我覺得非常開心,以後還希望有機會的話,能夠邀請您來跟同學分享這方面的經驗。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張卉君:我的榮幸。
吳宗憲:也謝謝各位夥伴耐心地把議題看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