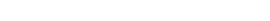講題:動物倫理的艱難:如何回應(無臉的)牠者
講師:黃宗慧/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系教授
動物倫理的艱難:回應的責任與逃避的原因
今天演講的題目從一開始就等於是告訴大家,我不是來提供答案的,而是要告訴你,動物倫理這道題很艱難,希望和大家一起思考,面對這個艱難的問題時,我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選擇。至於我們跟他者之間的關係,跟臉到底有什麼關係?待會我會引用哲學家的看法來說明。我先從我很喜歡的一首詩講起,Linda Pastan的Ethics(〈倫理學〉這首詩(彭鏡禧翻譯〉
多年以前的倫理課上
我們老師每年秋季都要問這個問題
如果博物館失火
你要救哪一樣,一幅藍布朗的畫
還是一個反正來日無多的老婦人?
坐不住硬椅子的我們
哪管他圖畫或老年
又一年選擇人命,次年選擇藝術
而且總是沒精打采,有時候
那婦人借了我祖母的臉
離開他慣常的廚房
逛到某個通風良好,半真半幻的博物館
有一年,我自作聰明,回答說
何不讓那個老婦人自己決定?
林妲,老師就說,是在規避
責任的擔子。
今秋我在一座真正的博物館裏我站在
一個藍布朗的真跡之前,老婦人囉,
可以這麼說,我自己,畫框裡的
顏色深於秋天
甚至深於冬天一土地的棕色,
雖然地上最鮮艷的元素焚透畫布,
我如今才知道婦人
和圖畫和季節幾乎是一體
但都不由學童來挽救
其實任何問題都可能有陷阱或有預設,我們要留心的是,或許很多倫理的問題根本沒有標準答案。在不同情境時,可能會做的選擇都不一樣。而詩裡這道題,詩人最後才發現,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個小孩子能回答的。因為即使當年老師的題目裡暗示老婦人來日無多,而藝術作品卻是出自名家,但是要放棄一條人命去選藝術作品,總是不可能沒有猶豫的。
這首詩裡有一句和我們今天的主題特別相關:「有時候那婦人借了我祖母的臉」。一向心不在焉對倫理課沒興趣的小孩,只有當祖母的臉出現在她想像中、當祖母進到這個博物館,成為要和藝術作品比較的選項之一時,小孩才會稍微對這個問題比較有感覺,但還是要等她自己成為老婦時,才會真正發現,我們其實難以界定生命、藝術何者較有意義;我們可以用二元的價值,說哪一個絕對的好嗎?
在教文學作品時,我常半開玩笑和學生說文學作品就是要教我們未老先衰,未老先體認老的心情,像這首詩就點出了詩人小時候本來無法設身處地,用別人的角度去想,但曾經因為「祖母的臉」而對這個問題稍微多了點在乎。當我們面對問題,尤其攸關倫理的艱難問題時,我們總是不想多想,除非是關乎我們的事。什麼時候會關我們的事?可能就是當那張需要回應的臉是我們所無法割捨的時候。至於那個眼神或那張臉為什麼會產生意義?每個人的答案又可能不一樣,而當我們願意去回應某一張臉的時候,倫理的可能性就產生了。
不過詩裡的小孩當初還是自作聰明地說要讓老婦人自己決定。這就像我們有時候碰到倫理抉擇的困難時,就會想要卸責,也是非常寫實的描述。以這首詩做一個引子是想讓大家去想想,很多時候我們是不是沒有比那個小孩好太多?我們都會想規避問題,除非像看到了祖母的臉一樣,我們也被某些切身的關聯性打動,或者是只有當自己換到當事人的位置,例如當詩中的小孩變成了老婦,才知道被假設時日無多、甚至被放棄,是很難受的。閱讀文學作品,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只有對與自己有關的事才能感同身受,而是在平常就能累積對事物的敏感度。
從一首詩開始今天的演講,我想說的是,倫理並沒有一套不變的守則可以遵循,而是因應不同狀況所下的決定,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了解哪些態度會讓我們不願意去面對倫理決定的艱難。在談倫理或動物倫理的時候,很容易遇到「不然你告訴我可以怎麼做、標準是什麼?」的聲音,尤其真正投身動保,很容易被質疑「你這樣沒有原則、邏輯不一致、只關心某幾種動物」,其實這些討論在西方的動物研究中,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更有彈性的想法,也就是有所謂「回應的倫理」(responsive ethics)這樣的說法,而回應(respond)這個字和責任(responsibility)之間是有關聯性的,能夠對他者做出回應,就是擔負了倫理的責任。
也就是說,任何的倫理決定,可能都是當下的回應,而不是有一套守則。有些人會對這種說法不滿,覺得這樣是一個藉口。可是也有不少哲學家、動物倫理學家都認為,這反而才是讓倫理不只是一個理論,而是有實踐的可行性的一套思考方式,甚至還有評論者為這套說法辯護,要那些一直要一套標準做法的人去想想:我們不是常常強調人跟動物之別,說只有人能回應,動物只能做出反應嗎?也就是依循笛卡爾心物二元論、動物如機器、動物沒有靈魂等想法,認為動物就算有一些反應,也是像機器人按照程式指令動作一般,不像人的回應是涉及心靈、靈魂的,是更複雜的,那麼我們現在為何又要求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守則,讓我們知道甚麼狀況就一定要做甚麼反應,那不就是變得像我們口中的機器人一樣了?
我自己是認同回應的倫理這種說法的,也就是我們可能要因應不同的狀況,因時因地制宜再做出決定,何況如果是倫理的決定,應該是你當下考慮各種情境跟自己的條件、再根據對方的需要而做出的回應,如果只是根據一套標準守則,那你根本沒有做任何的決定,還叫做倫理嗎?某種程度上,倫理就是包含了決定的,因為其中有某種承擔,而不是按照準則、按表操課,但這套講法不是大家都同意,有些人還是認為這樣沒有標準,太狡猾了。
實踐的難題:動物保護只是「選擇性仁慈」嗎?
尤其是接下來要講的,可能跟大家一般在追求的,例如做動保就要提倡眾生平等,對所有的生命都一樣友善對待,可能不太一樣。我要提出的反而是往另一個方向開始思考,就是先承認,我們現在對動物的態度,其實反映了眾生不平等,然後再試著理解,為什麼眾生難以平等,有沒有改變的可能。一些哲學家與批評家都認為,如果倫理真的要產生實效,要產生能夠操作的一套倫理思考方式,可能不是一下就把標準訂在一百分。所以我覺得比較可行的方式是,我們先去承認:倫理的決定可能非常困難,所以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會像詩中的小孩一樣想要逃避問題,但不是說承認困難就算了,我們還得進一步瞭解,周遭的哪些態度與要求會給我們繼續逃避的藉口,讓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好麻煩,不要去想好了」?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就是我們首先需要思考的。
我在台大每年開動物倫理相關通識課程,都會先跟同學談到這個問題,就是既然基於關心動物來修這門課,是否要能做到吃素?或者在其他課程需要做動物實驗,在犧牲別的動物生命時,又來關心另一些動物,是不是不符合修這門課的標準等等。但就像我剛才說的,沒有一套適用於所有人的原則,但我希望大家開始去學習,自己去畫出一條線,去思考哪些動物在界線範圍內,是目前的自己能力所及、可以也願意去友善對待的。這樣的方式並不是要把同學騙進來,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快就以為談動保只有全有或全無二選一。動保需要非常多人的加入,所以我走一個非常實際的路線,希望大家先去看到,到底什麼東西會阻礙我們去關心這些事情,做一個決定的時候又會遇到哪些困難。
接著想讓大家看一下一篇有點年份了的文章,〈鵝肝、龍蝦於高貴的慈悲〉(王飛仙),當時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那時候芝加哥通過禁賣鵝肝法案,主廚氣得跳腳覺得專業被侵犯,這也是動物保護運動時常會遇到的問題,很多人會覺得動保人士干涉、侵犯專業的範圍,諸如告訴主廚甚麼食材不能用,或建議設計師不要再使用皮草,都是不尊重專業,且干涉別人吃、穿的自由。不過我要說的重點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從禁賣鵝肝又聯想到當時某些超市禁售活龍蝦,但最後的結論是。這些關我們窮市民甚麼事啊?意指有錢有閒的人才為了自我感覺良好而抵制這些食物,但充其量這只算是選擇性的仁慈:「如果鵝肝跟龍蝦都要抵制,那豬跟狗也一樣可憐,那我們只能吃蔬果,蔬果難道不可憐嗎?強灌青菜肥料,這不叫虐待生物嗎?只怪青菜不會哭叫吧。」
這絕對不是一兩個人的偏激觀點而已,其實這種立場還頗為普遍,甚至是很多沒有吃素而來修動保課程的同學們也都會自我質疑,覺得自己是否正是這種選擇性的仁慈?然後接下來的反應可能就是,要回應這些質疑好累,那乾脆就不要號稱自己是動保人士好了,不要加入這場論辯。其實我們不妨問自己,就算是選擇性仁慈,但這表示在有仁慈的選擇時,我們做了如此的決定,那又有何不好呢?做不到全面的仁慈,難道就要全面選擇不仁慈的方式來達到邏輯一致?
以吃素這件事情來說,沒有吃素的同學面對的選擇性仁慈的質疑,而吃素的呢?如果被問到何以吃素,回答說是出自健康考量、宗教等理由,真的很少人會繼續追問下去,但若是回答是基於動物保護、環境永續的理由,那餐飯就會吃得很不安寧,因為諸如那穿不穿皮鞋毛衣、植物也有生命等質問就出現了,彷彿一定要吃素的人承認,就算吃素,還是不可能不傷害動物。同樣都是吃素,為何回答是為了動物,別人特別容易看不慣?甚至你回答說自己是基於某種神秘的理由吃素可能對方都還不會繼續煩你,覺得或許是個人隱私,獨獨對動保而吃素特別質疑,問題就出在人的防衛機轉,有些人認為,為不忍動物受苦而吃素的人像是在指責其他人都很殘忍,所以他們不如搶先一步,批評吃素者也會在其他面向上傷害到動物,如此一來好像自己的不吃素也更理直氣壯了些。
不論是剛剛那篇文章,或者類似的疑惑,如果是嚴肅的自我質疑,困惑於自己的邏輯不一致,我覺得那就確實是需要回答與思考的重要問題,可是如果只是以一種挑釁的姿態,說施肥是虐待青菜,或問說愛護動物的人要不要洗手?要的話那被洗掉的細菌可不可憐?這樣就不足為取了。我常覺得訕笑別人「反正你道德最高尚」,但不願認真思考自己何以有這種防備態度,對整個動保運動來說是非常負面的,因為十年二十年過去,動保人都還得花時間回答這些跳針般自以為很犀利的挑釁。
關於邏輯不一致的問題,在《深層素食主義》這本書裡也有談到,書中列出了一位受訪者的話:「我努力想做個純素食者——亦即完全不使用任何動物製品。那是不可能的。我擁有一台鋼琴,它有毛氈。這是橡膠,它的硬化處理過程使用到某種動物製品。一張打上亮光劑的漂亮桌子,使用了某種動物油……」這和減塑生活的困境有點像,一旦你開始注意想要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的時候,會發現生活裡到處都是。當然善意的動作還是要去做,從能做多少算多少開始,可是如果一開始設定的目標絕對要一百分的話,確實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就可能放棄了。怎麼面對我們的邏輯確實不一致?比較可行的方式是承認這個現況,然後去想,我可以做的是什麼,有時候若堅持這是一個全無或全有的選擇,像是比較激進的動物權人士,弔詭地竟會和完全不關心動物的人在某些論述上會變成殊途同歸,推出一樣的結論。
我列舉兩張素食網站上取得的漫畫圖示讓大家參考。
之前上課時在班上調查過,發現比較多人能接受的是訴諸情感的那張(當天現場調查也出現相同的結果),畫面中的人抱著牛,難過地說「抱歉我無法阻止他們」,意指無法改變乳牛的艱辛處境,但另外一圖片則是點出人們對待同伴動物與經濟動物的邏輯不一致,從而要求公平,所以安排了畫面中的牛豬雞和貓狗同桌而坐,貓狗這一方的台詞是,「如果人們虐待我們,他們就得去坐牢」,而經濟動物這一方則只有嫉妒的份。大部分的人為何會選擇情感訴求的那張圖而非要求公平的這張?因為那張圖片裡面說的就算是事實,卻沒有把不同的物種對立起來,這一張則製造了這樣的對立。大家可以想想,每次比較殘酷的虐待貓狗案件發生時,一旦有些人憤慨地因此上街頭抗議,是不是另些人就會有類似的反應?就是覺得經濟動物的問題根本沒有人理會,可是死了一隻貓的時候卻有人願意上街頭,真是不公平!這種想法本身完全可以理解,有些議題好像就是可以一呼百應,讓從事弱勢運動者不時有孤獨與不公平感的感覺,可是我必須說的是,諷刺或是對立的思維對某些真的只關心貓狗的人來說,並沒有用,有些人甚至只愛自己家的貓、狗,如果你說他有雙重標準,會比較像用一種公平正義的原則,指責對方邏輯不一致,其實效果不佳,最後很弔詭的是關心經濟動物的人和完全不在乎動物的人變得好像口徑一致,都在譴責只在乎同伴動物的這些人邏輯不一致,但經濟動物的地位其實並不會因此得到改善。
我覺得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很多人對同伴動物的情感確實不一樣,貓狗,特別是狗,就演化的歷史來說真的已經進入人類生活非常久,所以貓狗受虐才特別容易觸動很多人激憤或難過的心情,也因此會有比較大型的運動,去抗議這樣的事情。像之前曾有一次抗議虐貓的事件中,參與的人士用了一個標語─「今日殺貓、明日殺人?」,就立刻有人不以為然地以「今日吃牛,明日吃人」反唇相譏,看似是要凸顯經濟動物的問題就沒人願意為牠們大張旗鼓地抗議,但或許更重要的目的是指責這些只關心貓狗的動保人邏輯有問題,竟不惜「危言聳聽」也要連結殺人和殺貓的關係。問題是,虐殺同伴動物和殺人真的不相關嗎?很多刑案的犯罪者從殺小動物開始,或者為滿足攻擊欲,或者作為「預演」、「練習」,而家暴也經常同時伴隨有動物虐待事件,都說明了虐殺動物與殺人確實可能有一定關聯,而若是我們直接把這種惡意虐殺與肉食等同,是否反而淡化了其中個別行為者的殺意與施虐心態?其實非常多年前,我投入動保的契機,是因為台大校園內的流浪狗被潑硫酸,當時校內的學生們想要讓校方重視這件事情的方式,就是以「現在是狗,下一個會是誰?」的方式來爭取注意力,強調如果潑酸者不被揪出,或許學生也會有危險。這其中當然有策略的成分,確實在做動保運動,常常會強調,你今天會對動物下手,明天就有可能對人下手,「今日殺貓、明日殺人」這個口號也是如此,看起來好像是策略性的講法,讓不關心動物的人也因為關心人的安全而多少留意一下動物虐待的議題,但它同時也有合理的推論層面在;反觀「今日吃牛,明日吃人」,就算提出這個類比或許是因為想要求愛貓狗者應該邏輯一致地去思考肉食涉及的虐待問題,但某些對動保很惡意的人,卻剛好可以用來對動保形成反挫。其實動保運動要做的事情這麼多,大家可以分工合作,實在不需要變成互相攻擊與對立。
可是在台灣,同伴動物保護和其他動保運動一直有非常嚴重對立的傾向,前年到香港訪問當地動保人士的時候,曾問起香港那邊有沒有同伴動物保護跟野生動物保護互相衝突的問題?他們說,「沒有,我們做動保的人很少,同伴動物野生動物全部都是我們同一批人在負責」,我不知道這樣是值得羨慕還是值得同情呢?他們會非常羨慕台灣的動保進展得比較快,而確實,會有兩派吵起來的現象,好像是表示不同領域都有人投入,才會意見不合。可是我覺得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既然同樣想促進動物福利,就在共通的理念之下分工做自己擅長的部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很多時候力氣是拿來互相衝突、抵銷,這是台灣動保很可惜的部分。在台灣,關心經濟動物或野生動物處境的人不如關心同伴動物的人多,所以有些人覺得人類以雙重標準對待動物有失公平,這些完全都沒有說錯,甚至就是現況。可是不關心任何動物卻想貶抑同伴動物保護運動的人,用的也是這一套「邏輯不一致」的說法,於是多年來一直在邏輯不一致的問題上針鋒相對,所以我希望真正對動物有心的人,不要也掉進一樣的迴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需要對立,而是去面對,為什麼多數人給不同動物不同的待遇,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我們可以著力的地方。
我們要面對的現況就是,人對不同動物就是會有不同的態度,但至少我們可以去了解別人為什麼會選擇對某些動物做出某種回應,同時我們也要去想,要求邏輯一致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也許有些人覺得,就是要盡可能達到至善的境界,但事實是當你指望人人在動物倫理的實踐上絕對符合邏輯一致的要求時,多數人只會紛紛離開動保這這領域,會覺得,「算了,你自己往至善前進吧,我做不到」,那這樣的代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我們要想別的辦法讓別人覺得,關於不同的動物受虐問題,總有某個面向上有他可以做的事情,這樣才會有更多人願意留在這個領域。所以我會很實際的建議,就是即使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哲學界在談倫理的時候所說的,希望達到「無條件的悅納異己」(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這樣的目標,但我們還是可以先從有條件的悅納異己開始做起,就從最能引發你的共感的物種開始回應,這才是比較多人能夠被拉進來這一個領域的方式,何況倫理的決定總是偶然的(contingent),個人在當下某個處境,面對某隻動物時,所決定做出的最好的對待方式,就是一種倫理的回應。說倫理沒有一套準則而是有其殊異性的決定並不是一種狡猾的逃避方式,但這也不是說所有的倫理思考都等到那個當下的瞬間發生再進行就好,而是平常我們就可以多想想,自己對不同物種重要性的排序是怎麼形成的,如此也有助於理解,為什麼別人和你關心的物種順序不一樣。
倫理的臉:甚麼動物有臉?
我自己做動物保護運動,其實是從同伴動物開始,最單純的契機就是小時候和爸爸一起散步的時候,爸爸把路邊淋濕的小狗帶回家,後來家裡一直有養狗,這種早期經驗影響很大,更後來又養貓,但都還是限於照顧家裡的動物,不過因為喜歡貓狗,自然不忍心看到路上的流浪貓狗受苦,也開始做一些救援的工作,但接觸了同伴動物保護之後就會聽到一些質疑,就是剛才說的,為什麼只關心貓狗、邏輯不一致這類的質疑。你會發現很奇怪的是,甚麼都不做的人反而不會被質疑,但是一旦你開始做,就會被要求做到一百分,當然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現象,一開始只會有點心虛地問自己,為什麼那麼多生命在受苦但我獨厚貓狗呢?對其他的動物,雖然沒有那麼多的接觸、說不上有同等程度的喜歡,但是不是也有我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牠們的地方呢?如此才慢慢也關心起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等更廣泛的面向,我要說的是,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會影響他的選擇,不過這選擇並非一成不變不能擴大關懷對象。例如我們不妨進一步想想,之所以容易對某些動物產生共感,是不是因為牠們有臉?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看到更多動物的臉?
*哲學家談臉
這裡說的臉,重點並不是外表、生理上的結構,而是參考了哲學家列維納斯的說法,他認為人與人的倫理關係往往建立在臉,透過臉,他者以他的脆弱向我們發出了某個要求,召喚著我們對他者做出倫理的回應,所以你會發現,如果在路邊遇到向你兜售玉蘭花的人,你決定不買的時候,你通常不會看他的臉,不想看到他者的臉所發出的召喚。列維納斯的臉指的就是這種會要求你建立倫理的責任、希望你能給予倫理的回應的,一種面貌。
但是當列維納斯被問到動物有沒有臉時,他的回答是我們不能完全否定,說動物沒有臉,譬如說狗就有臉,可是他認為談論臉的問題時,重點還是人。動物的話,要界定牠們應該是依其他的特色,譬如像生命力、求生本能等等,因為動物的臉不像人那麼純粹,在訪談中他還說,他不知道蛇有沒有臉,這問題還需要更多的思考,我們可以看到,對他來說這兩個物種就有了差別,狗有臉、蛇不一定有臉。
我有一次很驚訝地在美國影集《六人行》裡看到這樣的橋段:其中一位主角的設定是素食者,有一集裡她問她服務於餐廳的雙胞胎姊妹說,「妳忘了嗎,我不吃有臉的。」不吃有臉的動物,乍聽之下很怪,但我們也看到了確實哲學家如列韦納斯就是從臉來談倫理問題,這或許也說明了,我們一旦覺得動物有臉,就比較容易和牠們產生共感,當然,我們願不願意看見動物的面貌、跟動物產生共感,其中可能還有利害得失的考量,或許不是在意識層面上真的去斟酌比較,可是只要你仔細地想就會發現,有時候,我們並不是沒辦法對某些動物產生共感,而是你評估過,發現這樣做划不來,例如和經濟動物共感,可能對自己生活與心情都會影響太大,因為牠們的處境太糟,而我們很可能無法立即為牠們做甚麼來改變現況,於是人的防衛機轉就會啟動,會自我保護,這時候,就算所面對的動物其實具備了召喚你回應的臉,你也會覺得目前自己還做不到、無法去回應。只要一步一步地檢視,回到自己的例子去想,就不難發現,為什麼自己對不同動物的共感程度有差別。
**愛有等差:你看見了哪些動物的臉?
接下來我要談愛有等差。一般不是說眾生平等嗎?為何現在逆向而行呢?因為我說的是對現狀的描述,而不是在告訴大家,差別待遇是對的或應該的。現實狀況就是,大家對不同動物表現出來的結果,說明了愛有等差,實際對待不同動物的態度上就是有差別的。自己在做動保時,也要不斷的面對自己的愛有差別心這樣的事實,然後才能去調整,了解到對於這個現況,我們並不是無能為力的。你在心裡面知道與某些動物比較親近、對某些動物比較無感,但在照顧動物和動物福利上還是有一些你可以為後面這類動物做的事,然後盡量去做公平的考量,這需要非常自覺的反省,承認自己的侷限之後要有警覺,也就是了解到侷限之後,還要思考有沒有改變的可能。像我自己家除了貓之外同時也有養烏龜,其實烏龜是野生動物,一般情況下不該被飼養,我養烏龜的原因,是看到牠們被百貨公司拿來當成親子娛樂活動的道具,撈烏龜遊戲池裡面有三隻烏龜都被玩得要死不活,所以我跟我妹去百貨公司向樓管抗議,之後把池中的烏龜都帶回去養,但一念之仁是不夠的,養烏龜需要專業知識與適合的環境,當時想得簡單,和很多人一樣沒有相關知識,就用常識想以為烏龜很好養,其實一開始就犯了錯,收養的三隻烏龜並不同種類,有一隻長尾龜兩隻巴西龜,牠們其實不宜養在一起,因為巴西龜比較強勢,直到幾年前長尾龜過世,急忙把另外兩隻烏龜帶去健康檢查,才從獸醫師那裡知道,自己過去飼養烏龜的方式都是錯的,這幾年我一直在彌補,盡量用心照顧剩下的兩隻烏龜,畢竟當初一開始養烏龜的時候,我很偏心,對牠們疏於照顧。舉例來說,家裡的每隻貓都是認真思考下取的名字,可是我們家的烏龜就叫大龜、小龜、龜龜,從取名就會知道當初是隨便養養、沒有什麼互動,名字也是因為當年烏龜要看醫生時,在掛號處被問到烏龜叫甚麼名字,才臨時取的。
如果問我比較愛烏龜還是貓,我還是會回答貓。畢竟我對烏龜的了解和互動、回應的可能,還是比較少,心裡還是覺得自己是個貓人,演講前我還在想,我今天來演講,可能要七、八點才能見到我的貓,覺得會想一結束工作就快點回家看到貓,情感的依附強度還是不一樣,可是我願意為烏龜和為貓所付出的醫藥費和時間、在照顧上付出的精力等等,卻可以是公平的,愛有等差我覺得是OK的,我覺得不OK的是因為愛的程度不同,就覺得比較不愛的動物不重要,所以沒有給予應有的環境和照顧,那就是有問題的了。
曾有研究指出,我們和動物的親疏遠近,和演化的順序有關。所以我們對哺乳類會比對鳥類或兩生類或魚類來得親近。以吃素的問題舉例來說,英文有個說法叫魚素(pescetarian),中文也有海鮮素的說法,問題就來了:吃魚怎麼會是吃素呢?但我們在卡通《馬達加斯加》裡也看到,愛力獅一度獸性大發、把其他的主角看成肉排,為了跟牠們繼續相處,不能吃朋友,怎麼辦呢?只好開始學吃魚,不能吃肉那就吃魚,而觀眾顯然也認為很理所當然,因為魚在電影理的形象與其說是動物,其實更接近食物。就眾生平等的概念所要求的公平性而言,當然完全說不過去,魚也是一條生命,但在飲食文化裡卻海鮮素這樣的說法,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目前的現況就是,我們對動物的愛是有差別心的。
而大家都偏愛比較「可愛」的哺乳動物當然也是現狀,至於原因,有些人認為這跟自然天性有關。知名動物行為學家勞倫茲曾表示,基於想要保護和養育小孩的天性,當我們看到動物表現出人類嬰兒般的特色時,很自然地會產生溫柔與愛憐的情緒,於是像嬰兒一樣頭比較大、雙頰鼓脹、眼睛位置較低、四肢較短以及行動笨拙的動物,就特別容易得到人類的青睞,例如企鵝就因為走起路來像學步的小孩一樣,受到許多人的喜愛。這種投射式的愛當然有它的問題,例如有些人覺得動物好可愛就一直想餵牠吃東西,這到底是在滿足動物還是滿足自己餵食動物的欲望?所以被人類因「自然天性」而偏愛的動物,也未必就真的能得到符合動物福利的對待,就像當初柏林動物園的北極熊努特,小時候因為可愛備受關注,在人群圍觀的目光下長大,但長大之後被認為不可愛了、就是一隻普通的北極熊了,人氣就下滑了,這對牠心理上的衝擊是非常大的,當時有些報導都指出努特有刻板行為與鬱鬱寡歡的現象,前幾年也以四歲的年齡就過世了。所以就算我們認為自己對某些動物的愛是出於自然天性,也不能認為既然是自然天性,那就沒辦法,我就是愛這些動物,不愛那些動物,因為自然天性既可能會讓不被關注的動物付出代價,也可能因為愛的方法不對而傷害了動物,所以自然天性不是用來當作藉口的,而是為了用來幫助我們了解:或許有些人如果比較偏愛某些動物,我們也不用急著去譴責他們的愛有等差,而應該去試想,這是否可能是自然天性的一部分。
如果自然天性有喜歡親近動物的親生命性(biophilia),那天性也包含恐了對某些生物的恐懼(biophobia),在Edward O. Wilson《生物圈的未來》這本書中裡提到,在人類久遠的歷史中曾有許多獵殺者渴望吃食我們,如毒蛇。而蜘蛛,昆蟲則等著咬我們螫我們感染我們,而微生物則打算將人體分解成惡臭的代謝化合物,因此雖然對這些生物的恐懼強度會因個人遺傳與經歷差異有所不同,但大約百分之三十的人表現出對這些物種與生俱來的厭惡。這種根植在天性的生物恐懼感自然也會使得我們不認為諸如昆蟲或毒蛇是需要我們給予倫理回應的,脆弱的,有臉的他者。換句話說,如果親生命性是天生的,那生物恐懼症也是。
回到一開始講的,臉的問題,如果要能辨識出他者的臉,前提是對方必須是脆弱的、需要我們回應的,那麼昆蟲真的很難被視為是有臉的。例如螳螂,可能是屬於有機會被認為是有臉的一種昆蟲,但文化研究者指出,螳螂倒三角的臉型與分得很開的眼睛反而成為電影中外星人形象的原型,也就是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可見我們對物種的態度除了受自然天性影響以外,也會受到文化形塑的催眠,在娛樂工業、大眾文化容易強化對特定的動物的刻板印象時,我們也就可能更傾向於對這些動物產生恐懼或厭惡,而這些被恐懼被討厭的昆蟲即使後來再經過動漫表現的方式加以萌化,有時候也真的沒有用,自然天性和文化形塑的影響很容易相加相乘,如果本來就討厭某個物種,譬如蟲,文化再現中習於將蟲與死亡的意象連結,再加上多數人原本恐懼蟲的天性影響,這種負面形象很容易就變得根深柢固了。
如果你在動物倫理的實踐上已經做了很多,想再試看看對不同物種的動物能夠善待到甚麼程度,或許可以思考看看,對蟲的恐懼是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克服的。純粹從理論上、動物研究的文獻整理上來看,已有很多討論提到人對於蟲無法接受的因素,例如蟲總是跟分解、腐敗的意象結合,還有蟲擬態的變形能力,讓人覺得很恐怖。還有昆蟲若以大量的數量出現,密集恐懼症者必定無法承受,又如對於即使世界末日之後蟲是還可能存在,蟲是人的繼任者這類的想像,都讓蟲如同我們的敵人。當然也還有其他原因,蟲也可能造成真實的危險、疼痛、叮咬,問題是多數人其實分不清哪些蟲是否會造成怎樣的傷害,還是一樣害怕,所以往往是先前的定見,勝過實際上生理上遇到的威脅。還有心理文獻表示,蟲的快速移動會造成暈眩,因此令人恐懼,總之,大家找到很多害怕蟲的理由,如此一來,實在不太可能把蟲當成有一張需要回應的臉的對象。
***為什麼牠們有臉,我們卻不願看見?
前面提到過,我們願不願意看見動物的面貌、跟動物產生共感,其中可能還有利害得失的考量,也就是說,就算許多動物不像昆蟲那樣,因為會引起我們的恐懼就不被視為有臉,但結果我們還是選擇對於有臉的牠們視而不見。例如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其實和同伴動物一樣,我們可以說牠們都有臉,但為何得到的待遇卻不一?每個人回去檢視自己對這些不同的動物議題願意投注的關心和能量,就會發現確實其中有差別,這時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
一般來說,確實還是同伴動物得到最多關心。我說這和利害得失的考量有關乍聽可能會讓人覺得很奇怪,但我要說的不是純然屬於意識層次那種很功利的考量。我們在幫助動物時或許並不會真的先問能不能得到甚麼好處,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人確實是在意回饋的,所以會在有意無意間,選擇投入比較能得到回饋的事情來做。有些人在貓、狗過世後就不願意再次飼養動物,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因為在權衡之後他們覺得負面影響多於正面,例如情感的負擔太大了,失去的時候太痛苦了等等。而很多人雖然害怕再次面對那種傷痛,但還是會選擇繼續養動物,這可能就是因為同伴動物的陪伴與互動所帶來的回饋,讓他們願意去承擔未來可能的傷痛。之前讀到一份美國的研究調查資料,指出許多婦女認為貓、狗比先生和小孩能提供的情感回饋還高,只在少數項目表現落後於人類伴侶,例如使用工具協助的能力,畢竟如果忘記帶鑰匙,先生可能可以幫忙開門,但狗通常卻沒辦法。這份報告讓我們看到婦女似乎特別重視同伴動物提供的情感慰藉,但她們卻也正是有些人拿來嘲笑的對象,特別是空巢期的婦女或愛心媽媽,被認為在情感上過度依賴動物,這些嘲笑並不公允,因為人本來就需要情感的依靠,為什麼認定只有人跟人的互動才是正常的呢?只要不是任性地投射對動物的愛、甚至到一種罔顧動物福利,只顧自己高興的地步,那麼和動物的情感互動都是值得珍惜的。整體來說,儘管很多人在考慮是否該飼養同伴動物時,或許會想到疾病照料上的經濟負擔和先前說的,情感羈絆帶來的負擔,但因為人與貓狗這類的同伴動物在演化的過程中已發展出很緊密的關係,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在評估利害得失之後,還是願意關心同伴動物這一塊,但野生動物因為和日常生活不是那麼貼近,能帶來的情感回饋也比較少,所以我們會看到,從事野生動物保育的,很多是研究這方面的相關專業人士,而從事野生動物保護也確實需要更多專業知識,因為一般人即使要談保護野生動物,恐怕也未必知道怎樣對待野生動物才不會造成對牠們的傷害。關心野生動物的人,或許可以從成功的救援中得到回饋與滿足,但野生動物議題也直接須要面對諸如與開放原民狩獵、開發山林等議題的衝突,所以「得」是否能平衡「失」,讓人願意持續投入下去,答案或許也因人而異。
如果投入野生動物保護的利害得失之間未必能平衡,那經濟動物的狀況應該是更不樂觀。英國有位藝術家Sue Coe,專門以畫作來關懷經濟動物議題,她所畫的經濟動物雖然有時有臉,有時數量大到失去個別性,看不出臉,但不管是哪種畫法,都是在控訴人對於經濟動物的無感,以及資本主義市場下動物如何更受到過度的剝削與利用。她的畫非常不討喜,引起不少抗拒,一般要不是認為她太愛說教,就是認為這些作品不算藝術,但她自己認為,她的畫之所以被認為沒有藝術價值、說教、情感氾濫,說到底,是因為人不想面對加諸在經濟動物身上的殘酷,不想看到有人替牠們發聲。的確,一旦選擇去看見經濟動物的臉,對牠們產生共感,通常似乎就得選擇不再吃肉,才有辦法覺得能幫助到這些動物,或許如此也可以帶來道德邏輯一致、問心無愧的感受,至少不會再被質疑何以一面做動保一面吃肉。但一定也會有負面的影響,例如在整體素食人口還不算非常多,素食選擇經常很有限的情況下,飲食上會有些不便,又或者是造成人際上的問題,被認為自命清高,還有諸如家人不認同、認為吃素會影響健康等等,只要曾經努力想要吃素的朋友,可能多少都遇到這些問題。現在有越來越多人朝彈性素、少肉這個方向去做,或許是一種折衷之道。其實,吃肉對很多人來說還是很難放棄的,許多人或許看到關於經濟動物在變成肉之前曾遭受怎樣的痛苦這類的影片時會難過,但卻依然無法就此放棄吃肉,或者等相觀的影像記憶淡去之後又開始吃肉。我覺得苛求所有想從事動保的人都要吃素其實也沒有必要,在放棄吃肉的行動上,常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個別差異性,有些人看到前面說的那些殘酷影片之後,說不吃就不吃了,但有些人就是做不到。那麼我們要選擇對於做不到的人說,你不夠資格做動保嗎?我覺得不需要如此,動保有很多面向都還是空白一片、有待耕耘的,做不到透過吃素減少對經濟動物的消費需求,還是有很多別的方向可以努力。
再來看實驗動物的問題。同樣用上面評估得失的標準來檢視的話,坦白說我不確定若和實驗動物共感,會有什「得」?因為在實驗動物的福利這一個區塊上,動保能著力的相當有限,無力感也就會更大。過去通識課程班上的同學曾說過,就讀的系所需要做動物實驗,但如果他們建議不需使用這麼多數量的動物——例如也許可以多一點人一組,共用一隻實驗動物,或是某些實驗不必要——很容易馬上被嘲笑,甚至把這種不忍貼上不夠專業的標籤。另一方面,在進行動物實驗的場景中,我們也總是不難看到有些人為了顯示自己很勇敢、不會因眼前所見有所動搖,就以嬉鬧的方式進行,這種對生命的受苦或消逝顯得無感、不在乎的態度,其實很可能是一種防衛機轉:因為不想表現難過、不想示弱,於是表現得麻木嬉鬧。至於那些誠實面對自己難過心情的同學,有些就轉系了,覺得無法進行動物實驗,覺得這個關過不了、走不下去,因為在整個醫學、科學發展還是認為動物實驗無可取代時,這種跟實驗動物的共感往往無法轉換成改變實驗動物處境的力量。在國外,以替代方案取代實驗動物的腳步稍微快一些,例如可以讓修課學生選擇簽署不做哪些動物實驗,但基本上實驗動物這個議題還是不太能容動保人士質疑或挑戰,有時候一質疑,就會被貼上反智、反科學、反醫學進步的標籤,會被反嗆,你生病了要不要吃藥,你敢不敢讓你的寵物,由不曾進行動物實驗的獸醫師看診?會有很多這類的阻力,所以就算覺得實驗動物很脆弱,符合先前說的,是有臉的動物,還是沒辦法回應,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說,就目前觀察到的現況來說,確實我們對待動物的態度與方式,是有位階排序的。
先前在一篇期刊文章上看到一種說法,就是建議想推動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福利的人,把貓人、狗人這些關心同伴動物的人先變成盟友,因為他們往往是最容易被打動、不忍見動物受苦的一群。回頭看看國內的現象,有些動保團體在往這個方向努力,但我們同時也看到部分野保人士與專注同伴動物保護的團體有某種對立的緊張關係,戲稱後者毛保、貓保、狗保,這樣的情形其實是不利整體運動前進的,因為一旦預設了對立,就不容易聽得見對方的聲音了,也很難有進一步的協商或結盟的可能。
動物倫理推動的關鍵:共感與知識缺一不可
說了這麼多動物在人類社會的排序,以及我們認為動物有沒有臉對排序有何影響,我想再談一下先前提過的,知識的有限。有時即使我們有心去擴展關懷的物種,去回應那些雖然有臉但是我們比較沒有接觸的動物,也可能不知從何做起,所以知識上的提升是必要的,否則對一些動物來說,很可能只是幫倒忙,因為你給予的援助可能不是正確的方式。例如許多鳥類救援的協會團體常年都會轉貼撿到雛鳥該怎麼辦的基本做法,平時就需要累積這些知識,才可能在動物需要救治時至少先提供基本的幫助,而不是只有共感。共感當然是很好的,對很多人來說也可能是從事動保的起點,可是沒有知識的提升,有些時候你確實會不知道怎麼去回應需要你幫助的他者。大家如果去搜尋新聞,會看到像下面這些錯誤的與野生動物互動的例子:把懶猴當寵物來飼養、到日本熊牧場餵熊吃蘋果、到貓頭鷹咖啡館和貓頭鷹合照。很多人會覺得動保人很掃興,比如日本熊牧場,這些熊很多已經被關到呆滯了,好像就是在向遊客乞食時才有一點朝氣,有些人就會覺得既然現況已經是這樣了,去看看熊、餵餵蘋果又有甚麼不對,畢竟只有自己一個人抵制也沒有用,就加入餵食的人群吧。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正是因為大家都覺得現況無所謂、或是難以改善,因此繼續消費繼續支持,問題才永遠不會改善嗎?說實在的,很多人沒有想這麼多,單純只是因為好玩,覺得看到熊站起來乞食拜託的動作很有趣、又可以滿足自己餵動物吃東西的慾望,不會思考到圈養野生動物來滿足人類娛樂需求涉及了多少問題。更麻煩的是,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會想這樣接近野生動物是因為天性中的親生命性。現代人因為跟自然太疏離了,於是會嚮往透過動物又再次接近自然的感覺,會覺得野生動物很有魅力。確實也有數據指出,在美國,每年參觀動物園人次比觀看職業運動比賽的人次高,動物園被認為是適合親子同遊的空間,儘管現在有些人開始意識到,許多動物園很可能是生命教育的錯誤示範,但對喜歡動物的人來說,當他們還沒有充分了解動物園中的動物因禁錮而受苦的事實時,他們看見了動物就覺得開心的心情,很可能是很真心很單純的。所以要被譴責的不是這種自然而然產生的情感,但要談動物倫理就也不得不很掃興地讓更多人知道,不能因為人類有這些情感需求,就順著人的需求決定動物的命運——例如以打造迎合遊客為主的方式來規畫動物園——我覺得群眾必須更嚴格地監督與要求動物園完成其號稱的教育與保育功能,動物園才會更重視動物福利的問題,至於動物園的存廢又是一個更爭議的問題了,在此就先略過。
畫出自己的一條線:你願意保護哪些線內的動物?為什麼?
其實,作動保最重要的是面對實踐的難題,因為講都很容易,在做的時候就非常困難,所以我想列出兩本書做參考,兩本都提到動物倫理的問題:哲普書《吃的美德》與科普書《森林秘境》,裡面同樣談到作者面對生命倫理的艱難時,他們所做的選擇。《吃的美德》作者的態度是,道德佈滿了陷阱,可是不能迴避的是我們都有選擇權,我們要做那個做決定的人,面對動物利用的問題,可以選擇固執不變或是盡力而為,而他自己認為,盡力而為就很好了,他寧願自己總是困惑不解、前後不一,但不願意因為一些過於簡化的原則、過於在乎道德立場一致,反而放棄去做出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樣只是變成對道德無感的人。他提到他自己「盡力而為」的方式,就是用痛苦/折磨(pain/suffering)來區隔,他主張盡力減少動物的折磨,但痛苦,就和折磨不能等量齊觀。對作者來說,折磨是一段時間的痛苦,某段時間累積的記憶,而痛苦則是所有動物不可能避免的一部分,所以造成痛苦不必然是罪惡,只要不要變成莫大的折磨。甚至他會區隔不同物種,認為創傷對狗的影響比對山羊深遠,所以前者受折磨的程度比後者高。至於獵捕野生動物,他也認為並非不能接受,因為動物死在人類手上並不比其他死法差,甚至被其他動物獵捕的折磨可能比人類槍殺大。關於這點我就不能百分百同意,因為還是得要看人類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採獵,有些捕殺的方式依然造成巨大的折磨。另外,他說如果叫他不要吃蝦子,他沒有辦法接受,因為他是用「有無受到折磨」作為標準,來決定自己的倫理態度,而蝦子的神經系統很低階,所以他覺得可以吃。某些物種更容易受折磨,他會優先放棄受折磨的物種,可是不是全面吃素。作者的結論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應設法終止牲畜受苦的不人道飼養。他反對不人道飼養,但只要是人道飼養、屠宰,都是他畫出來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想說的是,這套標準是他在使用的,可能不完美,但因為他不願意只是為了邏輯一致就對道德無感,所以給了自己這樣的一種解套方式,某些時候、他還是在消費動物,這他也誠實以對,我們當然可以質疑作者的這套原則是不是對自己要求太少(對有些人來說也可能是太多),然後訂出適合自己實踐的原則。
《森林秘境》的作者則有一套更嚴格的標準。在此書的推薦序中,吳明益老師特別引用書裡談到姬蜂的那段,因為姬蜂的生活史中有著造成達爾文痛苦不解的一種寄生行為:達爾文發現姬蜂會寄生在毛蟲的身上,而那種寄生模式是非常殘忍的,會把毛蟲活生生吃空。當時達爾文的女兒因生病夭折,他忽然對世界上是否真有上帝感到懷疑。如果上帝是仁慈良善的,為什麼會有姬蜂這種生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生存方式?他甚至因此變成不可知論者,有了所謂「惡的詰問」(the problem of evil),也就是質疑上帝若全知全能全善,為何世間仍然有惡。
針對達爾文這個質疑,神學上的解套方式,是說毛蟲沒有感覺,就算有感覺,也沒有意識和思考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的痛苦。但是作者認為,「毛毛蟲疼痛的性質和程度或許和我們不一樣,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動物感受到的痛苦比人類要輕,我們也沒有實證可以推斷,只有人類具有意識,這只不過是個假定而已。就算這個假定是正確的,也無法解答達爾文針對姬蜂所提出的質疑。這樣的痛苦會比較難以承受嗎?或者我們應該問:如果動物沒有意識,而痛苦是牠們唯一的感受,這不是更糟糕嗎?我想這麼問題或許是見仁見智,但我個人認為後面那種狀況是更不堪的。」他替毛蟲感到不堪,因為痛苦是牠唯一的感受,結果牠甚至沒有辦法意識到牠在痛苦。但是《吃的美德》的作者標準沒這麼高,可能就不會這樣為那麼多動物感到不堪,他說「人類以外的動物安於現狀,沒有對未來的計畫,逃避死亡只是出於本能,不是因為想實現未來的夢想。因此快速殺掉一頭動物並沒有剝奪牠們企盼的未來」,這種動物沒有未來的說法,也許未必能讓人認同,但這就是他在實踐上的解套方式,選擇性地關心他定義為會受折磨的動物。這兩種倫理態度,大家不妨進一步去比較與思考,然後再做出自己的判斷與決定。
小結:縱不能平等對待眾生,亦能給予平等考量
進入結論。剛剛一直提到愛有等差,但對於不愛的動物,還是有我們可以為牠們做的事情。我們不能平等對待所有動物,但是可以平等考量如何減少牠們不必要的犧牲和痛苦。《哲學家的狗》這本書曾舉過這樣的例子,他認為我們決不樂於見到一個小男孩把蒼蠅的翅膀拔掉,這無關蒼蠅痛不痛苦、有沒有意識,而是這個小孩這種無意義的殺害、這種滿足虐待快感的行為就是不對的,就像故意用小便對準蜘蛛沖掉牠,和如廁後直接沖水把蜘蛛沖掉相比,對蜘蛛來說沒有任何差別,但依然不是件好事,因為前者包含了對於自己輕視生命的態度與攻擊欲的縱容。長久下來,可能會對某些生命無感,甚至在某些生命消失時叫好,這種態度不值得鼓勵。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想把蒼蠅蜘蛛也納入關心的範圍,這未免強人所難。我想說的是,理想的狀況,不管動物可不可愛,我們都希望都做到眾生平等,可是實際的狀況是,眾生平等只是理想,所以剛才也只是在說,至少讓昆蟲「好死」一點,不是在談保護牠們。
對多數人來說,有些動物就是更容易得到友善對待,這時候如果只是批評他們邏輯不一致,說他們怎麼只愛可愛動物,對於推動動保是沒有幫助的,應該想辦法,讓更多人願意以關心可愛動物為起點,慢慢把範圍擴大出去。我常常覺得,台灣動保在「可愛」這個點上糾結太久,就算是事實,一直批評也不會改變,所以怎麼樣讓更多人看到這種侷限,做出改變,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從關心熟悉可愛的物種起步,進展到對於沒那麼可愛的物種我們也願意關懷,就可能慢慢推廣出去,擴及更多物種,去看到更多的動物其實也都有臉。
伊阪幸太郎的小說《沙漠》中有一段情節,是主角之一設想了一種情境,假設某人穿越時空回到過去,該地發生的疫病是他手邊的抗生素可以治療的,這時該不該顧慮使用了抗生素將造成歷史改變的問題?而他自己的答案是,「一個人若是沒辦法救眼前的人,怎麼可能解救更大的危機?歷史什麼的,去吃屎吧!只要能夠解救眼前的危機就好了,一個人若沒辦法幫助在眼前哭泣的人,明天怎麼可能救得了全世界?」
聽起來好像很偏激,但我的重點是,如果一直認為,既然怎樣也救不了所有的動物,不如算了吧,那麼不但甚麼都不會改變,甚至根本可能是藉口,就像小說中可以見死不救的人,很難讓人相信真的是為了人類未來的歷史考量,而更像是託詞。簡單來說,我們需要做的是誠實面對自己的侷限,雖然邏輯一致的倫理實踐期望的是達到「無條件的悅納異己」,但如同我一再強調的,我們總要從某處開始,從某種有條件悅納異己開始做起吧,否則未來再怎麼樣都沒有達到「無條件悅納異己」的一天。也就是說,先從你做得到的地方開始就可以了。所有倫理的決定都是沉重、艱難的,但有開始就有希望。最後我想借用錢永祥老師的話來做結語,我覺得台灣動保能夠進步,錢老師是非常先知、先覺的關鍵人物,他在某一次演講最後說,「我們把自己的生命稍微打開一點,就會發現很多動物會進來。草履蟲大概不會進來,毛毛蟲大概不會進來,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侷限。我們不是聖芳濟(St. Francis),我們沒有他那種和各種動物都能溝通的稟賦……。但我們可以跟很多動物互動。這不是說要大家一定要養狗養貓,或者一定要參加動物保護運動,一定要素食,不是的,只要我們把動物當回事,對它們多在乎一點,這就很好了。」這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低的要求,卻也是最可行的,這也是我今天想要對同學說的話。